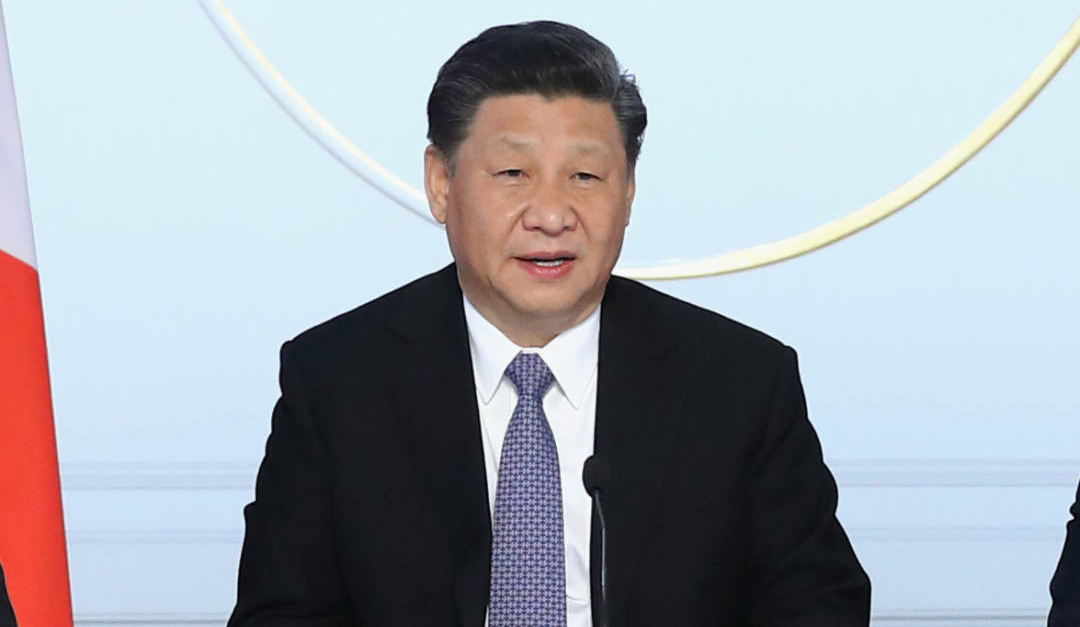(郭俊平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审判员)
我工作至今,已有40多个年头。记得经手的第一份起诉书,还是当事人用钢笔一笔一画誊写的,整个庭室只有4名法官,日均接待共计不过十余人次。
而现在,我所在的丰台法院立案庭干警总人数达29人,日均接待百余人次。当事人也都更多地开始选择网上预约立案,起诉信息通过二维码扫描,一秒不到就能全部读取到立案系统中。

(郭俊平与同事们的早期合影)
说到改革开放后法院系统的一次次改革历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同一位当事人两次截然不同的立案经历,它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改革给百姓生活带来的便利。
“破例”上门立案
1
2013年,我收到了一份邮寄立案材料,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当事人就住在法院附近的小区。
由于收到的材料非常杂乱,也没有写明案由,我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
电话响了许久才接通,接电话的男子略带呻吟地回答着我的问题。
寄来材料的老赵原来是一名工厂的车工,但一次下班回家的途中,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下肢落下了残疾。
但是对方一直不肯赔偿,积蓄入不敷出,治疗到了一半,老赵便回家休养。
由于近日病情加剧,他思前想后,想到了“告状”的出路。
2
当时即便邮寄的材料,本市的当事人也需要法院现场立案,考虑到老赵行动极其不便,经过再三思量,我决定上门去看看老赵的实际情况。

(上门立案)
来到老赵家,眼前的一切超出了我的想象。家门是大敞的,垃圾堆满了走廊,屋中充满了异味。
老赵告诉我,自己离异多年又没有子女,致残后家中无人清理,现在吃饭都全靠邻居接济帮忙。
从床上到门口短短几米的距离,都要忍痛挪动好久,最后干脆门就不锁了。
当时3月刚刚停暖,老赵家里冷得像冰窖,书记员帮老赵誊写起诉书的功夫,手就已经冻僵了。
我一边为他整理证据材料,一边询问他案情。前前后后两个多小时,才为其算清赔偿数额,并办妥了立案手续。
临走时,老赵问我官司打多久才能拿到钱,我告诉他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三个月之内审结。
回到办公室,我久久不能忘记老赵送别我们时期待的眼神。
之后,当我得知审判庭的法官当月就到老赵家开庭,并按照其申请,采取了先予执行措施后,才稍稍放下了心。
“照例”转至“7日调解室”
3
令我没想到的是,5年后,我再次收到了老赵邮寄立案的材料,原来由于旧疾复发,他再次起诉要求当年的肇事者赔偿后续治疗费用。
然而这次,我没打算再“破例”,不是嫌麻烦,而是因为我们立案庭有了更好的方法。
经过诉调对接中心,我“照例”将案件转至我院“7日调解室”驻卢沟桥社区的分工作站。

(立案登记制改革后操作网上预约立案系统)
第二天,社区调解干部和辖区的公益律师便来到老赵家了解案情,还安排社区志愿者解决了老赵卧床不起、出行不便带来的各种困难。
收到老赵二次立案材料的第二周,我便从诉调对接中心同事那里得知,“7 日调解室”安排了金牌调解员,联合工作站的社区调解干部一同来到老赵家上门调解。
跟上次现场开庭不同的是,这次对方没有到场。借助北京市高院的在线调解平台,通过线上调解的方式,双方足不出户便进行了对话。
一个小时不到,双方通过视频核对了全部医疗票据和其他材料。
最终,双方当场达成了调解协议,对方更是直接采取手机转账的方式,向老赵一次性支付了 1万9千元。
4
从视频里,老赵认出了我,他说记得当年是我上门立的案,还连声道谢。
看着如今窗明几净的屋子,还有老赵的笑脸,我开玩笑地说再也不用“破例”去上门立案了。
从“破例”到“惯例”,这一切得益于法院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效能,打通了矛盾纠纷化解“最后一公里”。
作为“社区吹哨,法院报到”的重要一环,“7 日调解室”驻社区分工作室巩固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通过要素式调解进社区、巡回司法确认进社区、调解示范课堂进社区三项服务扎根社区。
通过发动社会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来化解,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丰台模式更好地诠释了矛盾就地解决的现代版“枫桥经验”。
(供稿: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口述:郭俊平 整理:李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