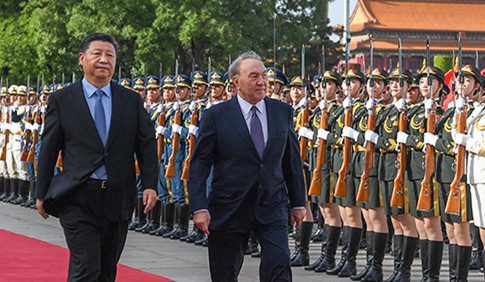2007年,我丈夫从新疆乌鲁木齐市考入离家一千多公里的边陲小城乌什县,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从此,我们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那一年,儿子刚出生。
“今天儿子会坐了”“今天儿子已经可以扶着床边站立了”“儿子开口叫爸爸了”“今天儿子会走路了,兴奋得在客厅来回走……”这个是警察爸爸在儿子成长缺席时,我每天通过短信息告诉他的小事,至今仍存在那部老掉牙的摩托罗拉手机里。
一年后的春节,丈夫回家探亲。刚刚学会走路的儿子从卧室探着小脑袋,好奇地看着,就是不肯出来,爸爸使尽浑身解数都不管用。无奈,爸爸将镶着警徽的帽子递给了儿子,儿子似懂非懂地接过帽子,摇摇摆摆地迈着小步子从卧室里扶着墙走了出来,走到爸爸面前,指着自己的小脑袋,这或许也是儿子对警察最初的概念。
一个星期后,儿子已经成了爸爸的小跟屁虫,连上厕所都要带着他。怕儿子伤心,丈夫趁着儿子熟睡时,踏上了返程的路途。睡醒后没有看见爸爸,儿子哭了整整两个小时,我只好指着墙上挂着的警帽告诉他,爸爸的帽子都在,待会就回来了。接连一个多月,每天下班时都可以看见儿子拿着帽子坐在客厅里等爸爸。那一年,儿子1岁半。
也许是在儿子的成长中,长期没有爸爸陪伴,儿子表现出了优柔寡断、胆小怕事。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要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家”。

警妈与儿子的合照
三年后,我通过公务员考试,也成为乌什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和丈夫成了同事和战友。我以为儿子从此将享受有爸妈共同呵护的完美生活。
然而,投身其中,我才真正体会到基层警务工作的忙碌,才发现我那个要给儿子一个“完美的家”的初衷依然是奢望。
一天早晨,我醒来后发现睡在旁边的儿子不见了,还听到厨房有响动。我飞奔到厨房,眼前的一幕让我既好笑又泪目——儿子踩着小板凳,抱着电饭煲,一勺一勺地吃着锅里的剩米饭,小脸蛋上沾着米粒。
看见我,他指着自己的小肚子说:“妈妈,肚肚饱了,我们去上幼儿园吧。”
“你饿了吗?怎么没叫妈妈给你做吃的?” 我心疼地搂着儿子问。
“妈妈太累了。”
那一年,儿子4岁。

儿子在洗碗
“妈妈,县上新建的电影院正式营业了,同学都说可好看了,我也想去。”对小县城的老百姓来说,电影院开业是件大喜事。我和丈夫约定好,下班后一定带儿子去看场电影。儿子知道这个计划后,特别兴奋。
可快下班的时候,丈夫突然临时有任务,都没有来得及和我告个别就出差了。而我,因为要临时开会,也没有按时下班。当我愧疚地打电话给在家等待的儿子支支吾吾解释的时候,没想到儿子却劝慰我说:“没事的,妈妈,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去,在家里也一样可以看电影,电视机里有好多好看的电影呢。”
那一年,儿子6岁半。
四年前,女儿出生,家务量成倍,工作任务也越来越细致而繁重。

全家福
今年“五一”小长假,平时生活中的一切都包办的公公、婆婆要去乌鲁木齐市检查身体,家里的大大小小事务都要自己做了,实话,要不是儿子这个小帮手,我一定会抓狂加崩溃。
一天下午,我下班后赶回家匆匆做好饭,把女儿安顿给了儿子就去单位加班。再回到家中,已是凌晨1点。我刚踏进门,女儿就用小手比在小嘴上,轻声地对我说:“嘘!轻轻地,不要吵醒哥哥!”只见儿子趴在沙发上沉沉地睡着,妹妹挨着哥哥,没有音响地看着动画片。儿子累了。
整个“五一”假期,儿子像个小大人,舍弃和同学们游玩的计划,寸步不离地陪伴照顾着妹妹,管吃、管喝、管陪玩。而他只有11岁。
“儿子,晚上咱们吃汤饭,你在回家的路上买3块钱的面、2个西红柿。”“儿子,今天是星期天,你带妹妹去图书馆看会书,顺便给妹妹买点零食。”……随着儿子慢慢长大,他成了我的依赖。

警爸送孩子上学
“小时候,我对爸爸妈妈不能陪伴我感到很失望、很伤心;当我慢慢地长大,懂得了爸爸妈妈是在为更多孩子过上平安幸福生活而工作,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是我的榜样,我长大了也要当一名人民警察。”这是儿子作文中的一段话。
我的儿子是无数双警家庭孩子们的一个缩影。他们的深夜,可能少有爸爸妈妈的陪伴;他们可能总是幼儿园里最后一个被接走的孩子;每一次家长会上,他们可能总是那个家长缺席的孩子;节假日里,他们可能总是独自度过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同龄人中“早当家”的孩子……
是懂事的孩子们支撑着我们的坚强!
我要由衷地对孩子说:儿子,谢谢你!你是妈妈心中依靠的小男子汉。(马索非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