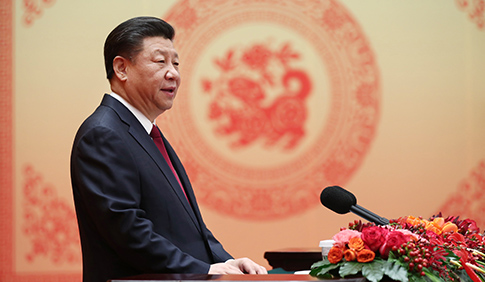春天来临,又到了鲜花盛开的时候,我履行着几年前的诺言来到花园,望着眼前一簇簇含苞待放的雏菊,我突然弄懂了一件事——所谓的生离死别,一开始也许都意识不到,直到彻底失去,永不再见,才会慢慢呈现,像树纹一样一圈一圈随年轮长进树干的里面,外人看不出,生命本身却知晓。
现在已是2018年的春天,姥姥已经去世一年多了。
姥姥的离去,让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悟衰老与死亡。当我望着姥姥的照片,无法相信那个在我童年里陪伴我最长久的人,坚持在饭后,拉着我出去散步,在鲜花开放时,带我一起去观赏,在我睡前,默默为我递上一杯热牛奶的姥姥,就这样永远见不着了。
菲利普·罗斯曾说:“衰老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屠杀。”我想,年轻时在山东穿着裙子、梳着长辫、能双手包饺子的姥姥,肯定想不到有一天自己会老成后来的模样。
我记忆中的姥姥身体一直很好,几乎没吃过什么药。直到70岁那年意外扭到腰,才使得健步如飞的她,什么都咬得动的她,一瞬间衰老。后来,腰好后的姥姥,渐渐背驼了,听觉也不行了,曾经一心想乘飞机出去看看世界的姥姥,不得不蜷居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每天看着活色生香的日子离自己越来越远。到后来,她终日躺在床上,更是老得与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
也许,人一老,就变小,不光身体变得瘦小,连精神也如此。有时候,我们一回去,姥姥就像孩子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怯生生地黏着,怎么也舍不得我们走。直到不得不起身离开了,姥姥便爬起来,拄着拐杖倚着门框摇手目送我们出院门,然后开始日日掰着手指等候我们下一次的到来……
寿则多辱,路暗且长。生命到最后总会像筛子,将年轻时候的兴趣、喜好统统筛走,唯让老来的日子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无趣!
一开始的时候,姥姥是舍不得离开人世的,但姥姥活到最后,总会念叨:“怎么还不死呢?阎王爷把我忘记了吧?”也许,对老人而言,死亡是一点点降临的。记得年前,姥姥和姥爷吃完午饭后,还睡了会儿午觉。可是等姥爷回来喊姥姥起床时,姥姥便已无法说话,无法直立。等我赶到时,74岁的姥姥,生命已像风中的蜡烛,只剩一点点光亮。但姥姥仍用仅剩的生命力,负隅顽抗,又熬了1天1夜,才熄灭最后的火焰。
即便如此,那时候的我也极不愿相信姥姥会走。所以,当妈妈在电话里讲,姥姥好像好些了时,我深信不疑。其实,那是姥姥的回光返照。
去世那天上午,姥姥从妈妈手里抢了馍,自己一点点掰碎,往口里塞,直到最后一点点碎末,也一一抹进嘴里。妈妈怕姥姥卡住,连忙喂点牛奶,牛奶喝了大半瓶,馍却怎么也咽不下。妈妈用餐纸包走姥姥吐出的馍,难过得背过身,不忍看姥姥大口喘气的样子。我不知道姥姥临终前遭受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我只知道,在她不好的日子里,我们坐在她身边,一一握着她的手,她侧歪着头,看不见我们,也说不了话,但知道我们在,眼泪便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后来,等到远在他市的妹妹回来,姥姥居然睁开眼睛,扯着嘴角心满意足地笑了。
次日,当街坊邻居陆续来看姥姥时,姥姥一直摆手。别人问她:“是快好了,不会死了吧!”姥姥摇头,然后别人又问:“是不会好了?”姥姥点头。
我目睹了姥姥这几年来,在死神的阴影下,一步步退让,终究退无可退的境况——当最后我给姥姥洗脸时,她的皮肤薄得像张纸,双腿瘦得只剩皮包骨,每喂几口水,就会呛得咳嗽。原来,到最后,我们连吞咽与言语的功能也要统统还回去,只剩呼吸。而最后的最后,连呼吸也停了,一个人便消失了。
但一个人的消失并不是完全的消失。为姥姥守夜时,妈妈对我说:“我脑海中你们的姥姥,是斜着嘴角笑的那个,不是脸颊塌陷、睡在病房里的那个……”姥姥走后,生活好似也逐渐回归正常。但总会频频梦见姥姥没有死,我到处给她找穿的,找吃的,然后,醒来,发现姥姥真的不在了——那个很会烧菜却不曾吃过一口我亲手烧的饭菜的姥姥,真的不在了。一想到这儿,便会恍若隔世般难受起来。
如果夜晚是星星的院落,思念就是洒满春雨的路,来不及等待,就被新露头的花草所覆盖。姥姥的生日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每逢她生日,我总会买上很多吃的穿的去看她。但今年的中秋,月亮还会那么圆吗?当我们吃着月饼的时候,姥姥会在天上看着我们吗?
很舍不得姥姥走,但也不想姥姥活着受罪。也许,正如妈妈所说的:“奶奶七十多岁了,天天望着天花板过日子,还得操心儿孙的事,活着也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所以,走了好,对她是解脱!”
是啊,时间在飞逝,万物都有终点。世界是我们想象的画布,生活像不停旋转的黑洞,随时随地裹挟着我们往一切不确定的地方去。爱至尽头,梦至虚无,不如把死亡当作瑰丽的梦境,把落日看成凄美的绝景。
在时光的倒影里,我们得学会与“理想之外的不理想”握手言和。在命运面前,该来的总会来,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没有人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至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去生活!
其实,衰老与死亡,自然得就像那天上的雨云,它能让天空灰暗,也能滋润万物。所以,面对它们,既不要哭,也不要笑,要试着理解,要学会接受!
虽然总是会有那么一些时刻,某些封存的记忆像巨浪一样扑面而来,让我们躲无可躲——就像睡着了所做的梦,没人能提前知晓,提前解密!
所以,我宁愿相信,三维之外定有那么一个空间,那儿的生命不像寒夜的冰,一碰就断,彼此间的情感也不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推就倒。那里有爷爷,有姥姥,有所有过去的过去,百年不变,千年不换,那里的人们永远不必为生活担忧,也不用为现实焦灼……
如今,姥姥真的走了,而我将带着她的某些特征继续活着,也许鲜花会凋落,绿叶会腐烂,但爱会在失去中一代一代经久的延续下去!(兵团监狱管理局 乔悦智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