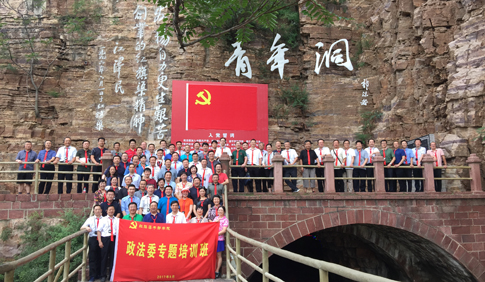以生命的名义
——一名宣传民警在纳雍张家湾山体崩塌现场的日记


8月28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张家湾镇普洒社区大树脚组突发山体崩塌。灾害发生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安排部署下,贵州省公安系统倾力投入抢险救援,截至8月30日16时,全省共投入救援警力1000余人,其中,公安民警800余人,消防官兵200余人;投入各种救援车辆110余辆,生命探测仪20台,搜救犬9头,无人机8台。参加救援人员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怀着沉重的心情,笔者走进救援现场,将所见所闻付诸笔触,表达对罹难者的哀悼,向所有参与救援的公安干警和社会各界人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第一天8月28日多云转阵雨
午餐。接到电话的那一瞬间,我被一口饭菜咽住了:纳雍县张家湾镇普洒社区大树脚组山体崩塌,几十户民房被埋,可能有人员伤亡。
在赶往现场的路上,我无数次想像着现场的情况,想像着受灾村民们一张张无助的脸庞,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无不透射着对生命和生存的企盼。
尽管设想过无数种场景,但当进入现场的那一刻,我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冷颤:中心现场已拉起了警戒线,沿着警戒线每30米左右站立着一个神色严肃的特巡警队员。省市县的现场指挥领导神色凝重、步履匆匆,快速穿过公路,进入中心现场。
我把相机镜头对准了眼前这一片望不到尽头的乱石、泥土和废墟,但是,快门却迟迟按不下去。目之所及,狰狞中渗透着几许凄凉。
艰难地涉过尖锐的乱石和泥泞,指挥员们登上一块巨石上,勘察、计算着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挖走眼前这堆积如山的泥石废墟。一群消防和武警战士拿着生命探测仪、牵着搜救犬艰难地搜寻;在一片废墟旁,一群特巡警队员或用手刨、用锄头挖,一点一点地往外搬运着石块和淤泥。这一刻,所有人都有一个愿望——泥石和废墟下的乡亲们一定要挺住。
从中心现场出来的时候,不足五米宽的通村公路上停满了各种车辆,交通有些瘫痪。显然,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牵动了社会各界的神经,纷纷涌向普洒。沿路的交警们像走马灯一样迅速穿梭起来,陆续增加的特巡警队员沿着公路拉起了警戒线,不停地劝阻着企图进入现场的围观群众。
豆粒大小的雨水伴随着夜幕倾泻下来,车灯、手电筒、手机灯逐渐亮起来,沿着公路慢慢形成一条蜿蜒的长龙,点点亮光宛如炬炬烛火,仿佛为罹难者哀悼。
回到山脚下的车里,已是凌晨三点,才躺下不久,又被一阵敲打车窗的声音吵醒,打开车窗一问,才知道是交警连夜清场,为即将进入的大型救援设备腾出场地。
这一夜,不知有多少人,彻夜未眠……
第二天 8月29日阴有阵雨
不到五点。
一阵轰鸣声惊醒山谷:挖掘机、破碎锤、救护车、通讯指挥车、电力保障车……陆续进入中心现场;观察组、搜救组、医务组、交通保畅组、秩序维护组……迅速到达岗位。
我沿着轰鸣声往下走,想要进入中心现场拍摄几张现场增援的照片,被维护秩序的武警和特巡警劝阻了,顺着他们的手指望去,崩塌后的山体仍不断有小规模的泥石坠落,在下方搜救的人员随时可能面临危险。中心现场内只有武警和消防两支部队的大型机器和人员在紧张搜救,而中心现场外的公路上,指挥部领导和被困人员的亲属心情同样紧张,等待着生命奇迹的出现。
中心现场旁两个女特巡警队员引起了我的注意,拍了照后,出于好奇,我走近了她们,想采访一下她们参加救援的细节,却被告知“现在正在执勤,如果要采访,请到营地。”在她们的指引下,我来到大方县公安局特巡警的营地。八九名女队员正在忙碌着,有的摘菜、有的煨汤、有的切菜,为大方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队员准备早餐。
通过交谈得知,大方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共有100名队员参加此次救援任务,其中有14名是女性队员。负责带队的是41岁的教导员刘雯岚,她是毕节市公安机关11支特(巡)警队伍中唯一的女教导员。在这次救援任务中,刘雯岚主要负责大方县公安局100名特(巡)警队员的后勤保障和女子中队的管理工作。
雨,时下时停。此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在泥水中行走了10多个小时后,脚上的皮鞋已经“开口”了,双脚被泡得冰冷麻木。在公路旁边的一家小杂货铺里买了一双仅有的女式雨鞋换上,又到指挥部就着矿泉水吃了午饭后,我继续沿着公路徐行。
在离中心现场200米左右的公路上,一群披着雨衣的公安民警奇怪的行为引起了我的注意:有的手持竹条撵着猪群,有的背篓里背着棉被衣物,有的肩扛着粮食,步履艰难地在泥水里前行。一打听,才知道是帮助灾区周边群众转移财物。
不知不觉已走了两公里左右,在一个三岔路口,交警和特巡警组成的联合卡口劝导组正在执勤。一位名叫梅艺的交警告诉我,他已经连续在卡口上站立了14个小时。
看着他疲惫不堪的面容,我心疼地对他说:“要不叫个人换一下吧?”
“人本来就少,哪个不辛苦!再说,我还年轻。我们市局的局长50多岁了,一直在这个卡口站了16个小时后还要到前面巡查。和他比起来,我真不算哪样!”
我顿时没有了任何言语,也失去了继续劝慰梅艺的理由,带着感慨离开了卡口。不远处的救援现场上,各种机器仍然继续震耳欲聋。我抬手一看,已是深夜一点半。
第三天8月30日多云
救援行动已经是第三天了,尽管已找到8名生还者和15名遇难者遗体,但离救援黄金72小时的结束越来越近,所有人的心越绷越紧。
因为睡不着,我早早就来到了救援现场,企盼着再一次发生奇迹。一阵凉风吹来,我一个哆嗦。赶紧跑进公路旁边的一栋民房里躲避。可是,眼前的一幕让我更加心痛:
两名特巡警队员倚在窗檐下,四名特巡警队员依次躺在靠墙的地板上,他们都睡得很沉。显然,昨晚一夜未眠。我不忍打扰他们,悄悄地走了出来。微风夹杂着细雨,身上更冷了,我又走进了几家民房。里面的情况和第一栋相仿,疲惫不堪的特巡警队员和公安民警横七竖八地席地而卧,都睡得很香。听见相机的快门声,一名民警一下子弹起身来,看见我手里的相机,慌里慌张地整理着衣服,一脸不好意思的神情,我冲着他做了“嘘”的手势,示意他继续睡后,我轻轻地退出房屋。
好不容易,我在离中心现场较远的地方找到一户人家,户主是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老大爷名叫张尽忠,已经76岁了。我向他打了招呼后,绕过地上熟睡的一名特巡警队员,找了一张凳子摆上电脑,准备写点什么。
我一边工作,一边陪张尽忠老人聊着天。期间,老人说:“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又是公安,又是特警,又是消防,又是武警,还有医生,共产党真是把老百姓当亲人啊……”
我一愣,这是这几天来我听到的最暖心的话了。是的,不管到什么时候,老百姓最信任的,还是我们的党!
无形间,对这次救援的信心又增添了许多。
中午时分,我写完稿子准备离开,可是老人不让,非要留下我吃完饭再走。我一看,一条长凳子上已经摆好了一盘诱人的腊肉和两盘炒菜,我知道,老人是诚心请我吃饭的,但越是这样我越吃不下去。环视了一眼他家简陋的房屋,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老人的邀请。
到指挥部吃过午饭,我再次来到距离中心现场近三公里的劝导卡口,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端着一口大盆,挨个给执勤交警和特巡警队员送上热气腾腾的蒸包谷。
在和休息民警交谈的过程中得知,老人名叫张发才,是一名退伍老兵。看到执勤民警又困又累,十分不忍心,不顾民警的推辞,将自己的三间屋子全部无偿让出来作为“临时警营”。
老人回家后,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张发才老人眼里闪动军人特有刚毅光芒说道:“我们老了,不能亲自到前线救援,只能尽自己微薄的能力做些事情,这些警察小哥连续干了两天多,累得着不住了,我看着心疼啊!”
我的心再一次湿润了:其实,我们一直和老百姓在一起,从不曾走远……
第四天8月31日多云
今天,参与救援的2000多名公安民警、干部群众似乎也从悲痛之中走了出来,全身心投入救援行动。
一大早醒来,我电话联系到了连续工作了三天两夜失联人员排查组组长林义和民警赵朝阳,想了解至目前为止的准确信息。见了面,满脸倦容的林义和我聊了两句后又被一个电话调走了。赵朝阳揉着双眼出门对我说:“你要问什么?最好简短一点,后面还有好多事。”
通过交谈,我大体得到了这么一些信息:三天来,失联人员排查组共对现场3个组59人218人的信息进行核查。为了确保信息准确,为指挥部决策提供详实依据。由15人组成的失联人员排查组分成了三个小组,分别对失联人员家属进行面对面了解,找现场周边目击者询问事发情况。同时,以户籍人口为核心,逐一核实外出务工人员,并且通过目击者留下的视频资料认真查找失联车辆和人员。对需要调查的人员做到户户走访,人人见面,仅这个组三天就走访120余人。最后还协助完成了现场复原草图。
我问赵朝阳:“连续工作这么长时间,累吧?”
“累是肯定的,心无杂念就好了!”赵朝阳这样回答。
赵朝阳口中的“心无杂念”,也许只有参与救援的人才懂,那就是“哪怕多救出一个人,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告别赵朝阳,我拨通了毕节市公安局特巡警队伍总负责人王子能的电话。随后,我得到了一组数据:全市所有县、区共有682名特巡警队员参加了此次救援,负责对三公里的区域进行秩序维护,疏导围观群众,协助搜救被困群众,帮助群众转移财物,巡逻值守。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多名队员不同程度受伤。
回到指挥部的时候又是深夜一点,终于有了一个地铺,结束了我的“汽车旅馆”生涯。与9名战友一同躺在一户人家堂屋的地上,我辗转反侧。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四天来的点点滴滴:那一张张熟悉而或陌生的脸庞,那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那一个个雨中匆匆而过的身影,那一盏盏闪烁不断的警灯,最后都幻化成现场一张张请战书上一枚枚鲜红的手印,升华成闪亮党徽下高高飘扬的八个大字:大灾无情,人间有爱!
尽管我已进入梦乡,但我深信:这不是梦。(郭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