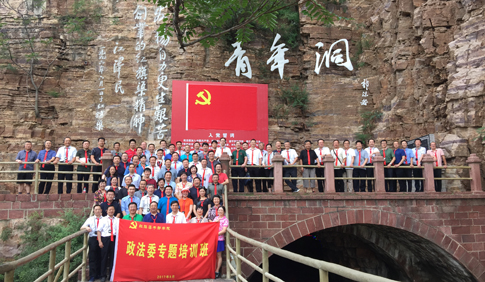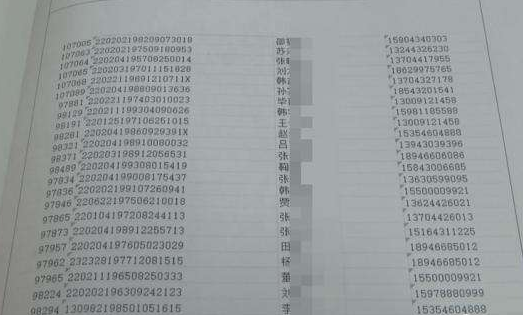淮南市八公山区八小的法制副校长贺叔生病了,教导员老谷便让我代他去上一节法制公开课。我问了下老谷:“是给几年级的学生上课?我好针对性的准备课件呀。”老谷霸气回应,不是几年级,是整所学校!我一听,好家伙,这场面有点大啊,得好好准备,不能在几百个孩子面前丢咱公安的脸。于是我花了一晚上时间找材料,做课件,第二天中午还趁着午休的时间彩排了几遍,下午顶着双朦胧困眼就被老谷带去了八小。
学校在八公山脚下,一路走去环境甚是幽静,我忍不住夸了几句,老谷一脸自豪:“这是我的母校啊!”我随口一问:“现在学校有多少人?”老谷自豪的表情有点僵在脸上:“大概,大概有四五十人吧……”“瓦特(what)?不是说全校师生吗?”我震惊地看向老谷,“是全校的啊!”老谷一边说一边爬上了教学楼暨办公楼楼梯,我张着嘴巴跟在他身后走进了校长室。校长姓凌,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我以为老谷在跟我开玩笑,于是趁着凌校长给我们倒水的空档向他求证学校到底有多少名学生。凌校长伸出3个手指头,一脸认真:“我们学校一共有学生39人。今天有3个请病假的,所以听课的一共有36人。”我扶了下快“惊掉”的下巴,确定老谷没有开玩笑,开始接受只有36个学生来听课的事实。
等我们走到电教教室,果然看到年龄参差不齐的学生们,搬着小板凳做成四五排,每排六七人。老谷到讲台上做了开场白,孩子们热烈鼓掌;我说了句大家好,孩子们就更加热烈鼓掌。这真诚的欢迎感动了我,大概在孩子们单纯的心里,穿着帅气制服的警察都是英雄式的人物,所以才有这么热烈的回应吧。
孩子们上课的情绪非常高涨,每次互动,都把小手举得高高的,一脸期待被点名叫起。讲课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一个是当我讲到“走失了该怎么办”时,问大家有没有不记得爸妈电话的。我原本以为不会有几个孩子举手,出乎我的意料,竟然有8个孩子弱弱地举起了小手,这个比例实在不算少,我问了下才知道,这几个孩子父母都在外地打工。想起之前凌校长告诉我的,全校39名学生中,有将近一半的都是留守儿童,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另外一个是,一个小姑娘咳嗽了,小脸憋得通红,因为时间比较紧,我没有停下讲课,而是走到她身边,用手帮她顺了顺背,又安抚地摸了摸她的头,小姑娘羞涩地笑了,谁知道这个动作刚一做完,教室里瞬间响起好几声咳嗽,我心里有点想笑,孩子是在用这样笨拙的方式求关注,求关爱,虽然有点幼稚,但更多的是可爱。
第三件事就在讲到禁毒知识的时候,我放了一张图片给孩子们看,图片分两半,一半是正常人的半张脸,红润帅气,手里托着房子和幸福的一家人。另一半是“瘾君子”的脸,瘦骨嶙峋,手里抓着针管、药品还有一朵妖艳的罂粟花。我问孩子们,知道这是什么花吗?孩子们踊跃举手“我知道!我知道!”我挑了一个看上去是四五年级的女学生,那小姑娘自信地回答道:“玫瑰花。”听到这样的答案,旁边的听课老师都笑了,可是全校没有一个孩子来反驳“这不是玫瑰花,是罂粟花”,这其实反映了法制教育的缺失。同样缺失的还有青少年性教育,在讲到校园性侵害时,后排几个高年级的女孩子互相看了几眼,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悄悄低下了头,这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继续说下去了,当然,我依然“顽强”地坚持把话题说完了,因为我知道现在儿童的性侵害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加强防范意识不容忽视。

上完课后,我与36个孩子照了一张“茄字剪刀手”全家福,纪念我的第一次“全校”法制课。拍照的时候有个孩子悄悄地搂了我一下,我把她抱到我的腿上,她笑成了一朵小花。学生少也有少的好处,一节课上完,大家就彼此熟悉,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很温馨。
临走前,我们与凌校长说了会儿话,他说这样形式的课他和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希望以后可以多开展几次,他也会努力地招生,让学校生源扩大一点。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个年级的孩子趴在窗口往我们这看,我笑着冲他挥了挥手,等我们准备走时,再往那个窗口看去,那里竟然长满了小脑袋,好多小手冲我们挥啊挥,依依不舍的神情都写在了他们稚嫩的小脸上。我走了老远,回头看时,还能看见孩子们花儿一样的笑脸。
(王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