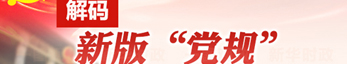北京一中院召开“忠法论坛”推进司法改革

北京一中院第五期“忠法论坛”现场。李佳 摄
裁判文书是法官的名片,也是彰显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的“宣言书”。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提升裁判文书的质量,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期“忠法论坛”,资深法官、青年法官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裁判文书的记载与说理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与会人员分享和交流对于裁判文书改革的认识思考与实践经验,展示裁判文书记载与说理改革所取得的成果,让裁判文书更好地承载起“看得见的司法正义”的功能。
说理无止境 改革在路上
北京一中院在裁判文书改革中起步早,有良好的基础。该院研究室主任胡嘉荣在发言中,详细梳理了北京一中院推进裁判文书改革、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基本情况。
1999年该院设置专门的裁判文书阅览室,将已审结的裁判文书汇编成册,供社会各界人士查阅;2001年以来先后编辑四卷《优秀裁判文书选编》供法官学习交流;2006年成立专门的裁判文书校核室,对拟印发的文书进行语言文字上的把关;2008年,制定《关于加强司法公开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强司法公开工作实施细则》等,强化裁判过程与说理的公开。
并在2011年制定《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出台强化裁判文书说理的三条硬性措施;2012年制定《关于加强审判工作促进案结事了的指导意见》,强调裁判说理的针对性;2014年出台《关于探索推进裁判文书改革的指导意见》,并提出《关于强化裁判文书记载与说理的八项措施》,强化对裁判文书质量的考核。
裁判文书的说理改革要适应司法工作的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胡嘉荣认为,根本上还需要法官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切实提升说理能力,勇于探索,不断深化。
北京一中院院长吉罗洪在论坛上表示:裁判文书是彰显法治精神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宣言书”,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裁判说理是联系社会公众与司法的“感情纽带”,说理的意识和方法需要不断巩固、提升;裁判文书也要适应法治社会发展的要求,需要持续不断地改革完善。
裁判文书说理: 理念与逻辑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制订的“一五改革纲要”中,就对裁判文书的说理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四五改革纲要”又专门针对裁判文书说理部署了改革任务。
可是裁判文书怎么说理,如何让当事人接受、社会大众理解和法律研究者认可,一直是困扰法官的难题。
北京一中院民四庭法官杜卫红结合商事案件的特点,提出了商事裁判文书说理要体现商事审判理念,“在商事审判中,通过裁判说理展示立法精神和价值取向,其作用不仅体现在明事实、断是非、定责任,更起到对相关的市场秩序进行规制,充分体现商事审判指导正确的价值取向的作用。”
杜卫红认为,由于商事交易模式繁多,现有的法律规定往往无法直接调整各种纠纷,这就要求法官根据立法精神和国家现行政策,发现和挖掘契合市场经济运行特点的裁判规则并阐述理由。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是对商事法官裁判能力和裁判说理能力的挑战和考验,客观上要求法官通过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进而创造性地适用法律。”杜卫红说。
不同审理程序的裁判文书,说理特点也不同。北京一中院审监庭法官孙锋结合再审案件的特点,从裁判文书说理的逻辑性上,发表了自己的认识。
“再审裁判文书的说理在逻辑性方面的要求更高。” 孙锋说,一是再审是终局性诉讼程序,需要在原判基础上对已有的主客观素材进行逻辑编织,或纠正、或补强原审裁判说理。二是再审裁判文书不仅要说服当事人,还要说服原审法官,从而使其纠错功能得以在预防层面上得到延伸。
孙锋认为,在再审裁判文书的说理上,法官应充分阐明和论证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事实、理由和判决结果融为一体,以使裁判文书的说理具有权威性的同时兼具科学性以及可供检讨的容许性。
团河人民法庭法官杨磊着重谈了二审发回重审裁定的说理。他认为,二审发回重审的功能在于保护当事人必要的审级利益,使得当事人可以充分行使辩论权和处分权。由于二审发回重审并不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有终局性的影响,只需要明确一审存在的问题。
“应当严格区分程序性发回重审和事实性发回重审,对于前者,在严格限定几种严重程序瑕疵才能发回的基础上,在论理时既要论证程序为什么是错误的,还应当明确如何予以纠正。”而对于后者,杨磊说,应当注意监督指导的边界,一般仅论述基本事实为什么不清楚,对于基本事实具体是什么、如何处理则不予论述,从而区别于构成改判的情形。
本次论坛的点评嘉宾、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认为,裁判文书改革要回到诉讼的本质,即要解决纠纷。裁判文书说理首先要明确目标,说理的首要目标是为了说服当事人,当事人没有异议或者在审理中已经说服当事人的,就可以不用在裁判文书中展开说理了,要处理好审判过程中的说理与裁判文书说理的关系。
裁判文书记载:方法与技巧
北京一中院出台的《关于强化裁判文书记载与说理的八项措施》,强化了裁判文书中关于程序性事项的记载,对于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密切相关的程序事项以及当事人提出的程序性申请,裁判文书应全面完整记载。
“强化、细化裁判文书对于审判程序性事项的记载,是体现审判程序公正、保障被告人人权以及规范诉讼参与人行使权利的重要举措,使‘固化’的审判活动重现在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面前,便于其监督,对法官严格依法办案也是有力的约束和促进。” 北京一中院刑一庭法官张鹏围绕刑事裁判文书对于程序性事项记载改革发言时说。
在刑事案件中如何对多名被告人实施的涉及多个罪名的多起犯罪事实进行清楚、准确、简洁的表述,是撰写刑事案件裁判文书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刑二庭法官王岩在发言中,建议区分一名或多名被告人实施的仅触犯一个罪名的多起犯罪事实的表述,多名被告人实施的触犯多个罪名的多起犯罪的表述和多名被告人、多罪名互相交叉、案情复杂案件犯罪事实的表述三种不同情形,采取综合表述和分别表述的方法,兼顾全面完整性和简洁概括性,做到繁简得当。
裁判文书制作:繁简分流
立案登记制改革后,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大幅提升。北京一中院2015年1至9月,9个审判庭新收案件同比上升幅度均超过10%,其中,行政庭为32.7%,立案庭为102.3%,申诉庭为58.4%,团河法庭为52.7%。
在案多人少矛盾仍然存在并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是有效的化解措施。
该院民一庭法官张磊认为,繁简分流并非法官工作的目的,而是提高审判效率,满足当事人需求,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裁判文书繁简分流的核心价值取向应当是根据案件类型、当事人诉辩内容、争议焦点的不同,在判定是非与辨法析理之间寻找契合点与平衡点。”
张磊说,一是繁要繁得到位——重在分析透彻,基础规范分析、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有争议要件事实的认定应当“繁”。二是简要简得合理——重在有所交待。诉辩理由、无争议事实及非要件事实、释明环节应当视情况简。(高春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