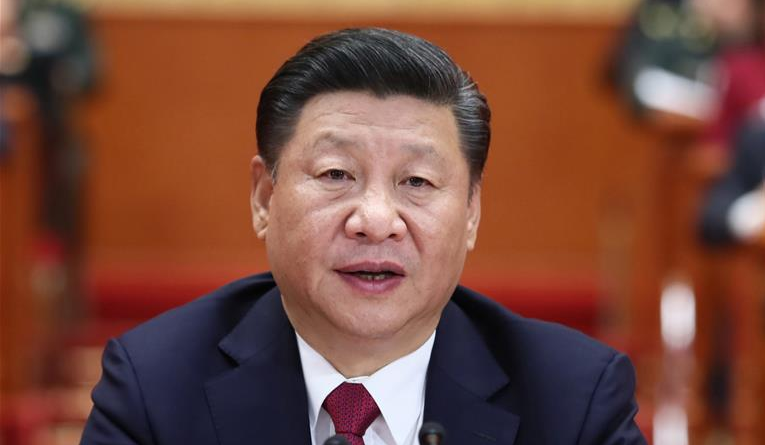大学毕业来兵团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在青春洋溢的幻想里,刑警的威严才是自己该拥有的姿态;再不济,也得当一名治安警,当初实习的时候,师父就是治安中队队长,一起见证和经历过街巷里的苍茫。
但世事难料,凡事都能按照想象去发展,那是小说,是电影,不是人生。到兵团没两个月,正好赶上公务员招录考试,我瞅着职位表上的数字盘算——考别的地方,万一进了面试既得请假还得考虑交通食宿,反正是“试一把”何必声势浩大,就选本地的、招录人数多的岗位。况且,网上的招录文件里写得很清楚,岗位是“第一师监狱管理局”,错不了。
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我以报考岗位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了,但岗位不在“第一师监狱管理局”,而在据说是整个系统唯一不通公路的一个监区。或许随遇而安,或许无可奈何,来不及迟疑,崭新的生活就此开始了。
既然一切都是新的,包括所在团场的名字都叫“新开岭”,自然少不了工作上的适应、心态上的调节。生活节奏虽然没有城市里那么紧张,但也那里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则:除了睡觉和吃饭,差不多一整天是与服刑人员在一起,点名、熟悉基本情况,按部就班、确保安全,就是美好的一天。
两年后因布局调整,分散在团场的关押点集中到了城区。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灯火通明的院落就像殿堂一样,驻守在城市的边缘,遥望繁华,聆听喧嚣。
与很多监狱民警一样,我也有值夜的任务。20点,月色渐起的时候上岗,经过与夜幕和时间的鏖战,清冽的威风会和初升的朝阳一同到来,交接、下班,好似完成一道轮回。
说实话,值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的,但并不意味着会相安无事。监舍楼虽然不大,但足以容纳人生百态,而值夜,便是换了一种形式的对话——与深沉的夜,也与复杂的心。
记得有一次,监区还没有搬迁,领导安排我到一公里之外的监区菜地值夜,晚上那里虽然没人,但农资设备都在,正值冬天,大棚里的蔬菜也得注意保暖,夜里还要看看炉子闷好没有。
拿着手电筒巡视完一圈,回值班室想喝口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原来一辆货车在倒车时把栏网柱子给撞歪了,跟司机一起费了好大劲恢复到差不多原样。第二天跟领导汇报,领导说,栏网没破损,再添些土压实些,就好了。
当晚也遭遇了突然停电。前些年,团场、连队的电力供应并不是那么完善,当漆黑一片的混沌来临时,我会慌乱,守着值班室的炉火,会莫名感到不安,之前听到的“菜地曾是乱坟岗”的传闻会不由自主涌到眼前,似乎在巨大的天幕之下,真有一些不可名状的事情出现。
后来,领导和同事都不止一次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别怕,咱这一身藏蓝,是“辟邪”的,跟传说比起来,更可怕的是人心,只要坐得正行得端,就什么都不用怕!
聆听喧嚣。
进城后,每次值夜,我都喜欢在监舍楼前的空地上驻足一小会儿,哪怕只有一两分钟,无论是星光璀璨,还是朝阳烂漫,都令人感到周身顺畅。 塔克拉玛干的长风拂过塔河岸旁、天山脚下,刚好将天空吹出一些深邃、一些湛蓝,艺术品一样的画面,让躁动的内心,以及如地下暗河般涌动的不安,归于静谧。
没有肆意生长的惊心动魄,唯有年轻的日子,如同摆在案头的日历,在一页页记录岁月,把云淡风轻连同心中的光,连同苦辣酸甜一起品尝。
这座城市不大,就跟很多监狱警察的工作一样,不起眼、很普通,然而,无论是值夜的执念,还是执勤的执着,总能编织出梦想、书写出安定。日复一日中,很多人不知不觉就干了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不由自主会感慨——服刑人员是“有期徒刑”,我是“无期徒刑”……
但转身听到一句“警官,谢谢!”也会朝着新生的灵魂会心一笑;解开一个心结,让家人重新接纳昔日的“浪子”,也会成就满满;登上舞台歌声嘹亮,唱出忠诚和信仰,也会热血沸腾,自信昂扬。
心中有光,城市再小也囿不住闪耀的未来;未来有梦,守夜再苦也挡不住精彩的人生。有时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只要活得漂亮,又 何惧黯淡?
用庄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边缘化”的事情,不管别人如何,脚踏实地坚持到底把事情做好,才能真正发现生活的乐趣、人生的价值。用敷衍了事、应付凑合的态度怎么能期待拥有一个意趣盎然的未来?
让自己阳光起来的意义,一个是强大,一个是自信。身有力量心怀光芒,才有把握迎接灿烂和辉煌,披荆斩棘的无惧无畏,才更应该是梦想鼎沸的标配。
也许,坚守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无论困难多么多、任务多么重,它都会在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它的汗水与欢乐,早已融入了血脉,厚重了灵魂,添彩了人生。
也许,挚爱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有了软肋,也有了铠甲,有了心安的归宿,也有了无时无处不在的敬畏。它的沉淀是踏实和光荣,它的升华,则是永恒的希望。
希望守夜人的执着与梦想,夜夜安详,唱出芬芳;希望每个人的山川与海浪,日日回响,一如既往。
(杨文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