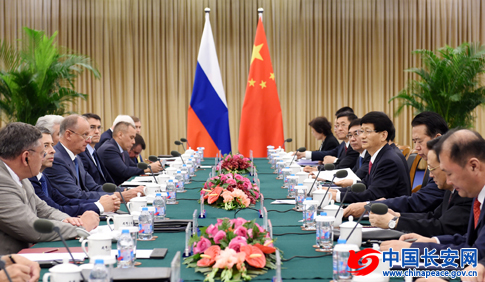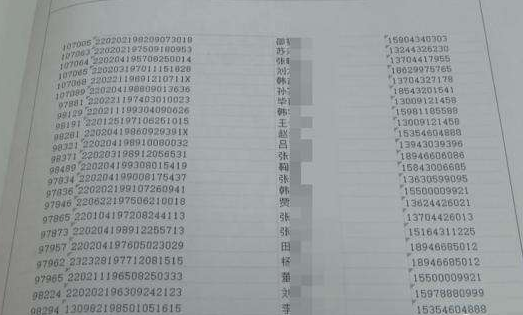幽默先生与喜剧大师
一天,我向一位资深法官请教问题:法官的作用是什么?他略一思索就给出了答案:“法官是幽默先生和喜剧大师。”我对他的回答感到好奇。他解释道:诉累是沉重的,诸多纠纷往往带有“悲剧”色彩。而法官的作用,则在于将“悲剧”改编成“喜剧”,将诉累幽默成轻松。下面就是他讲述的案例故事。
两棵树的故事
在淝河之畔,有一个偏远的集镇。集镇上有一个简陋的法庭,管辖着附近三个乡镇的民事案件。这些乡镇的周围分布着大片农田,种地的农民既勤劳又朴实。也许是长期附着于土地的缘故,他们对自己的一草一木都有着超乎寻常的执着和感情。这里所讲的两棵树的故事,就是这种情感的体现。
这是第一棵树的故事。
原告和被告是同村村民,都姓陈。两家的纠纷是由于争执一棵树的所有权而产生。这棵树只是一棵杂树,有碗口粗细,长得也不直溜,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经济价值。杂树原先生长在原告的地头,后由于耕地调整,原告的老地头变成了被告的土地。两家为了争树,发生了不少纠纷。最严重的一次就是被告的老婆在地里干活时,原告的家人从背后窜上去就打,结果将被告老婆打伤。双方闹到派出所处理,从而结下了根深蒂固的矛盾。
原告为了争夺树的所有权,起诉到法庭,主张这棵杂树是其栽植和培育,应判归原告所有。被告则否认杂树系原告所栽,主张是自然生长形成,既然长在被告的地头上,当然应归被告所有。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下。这位资深的法官正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只不过他当时从大学毕业时间不久,还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经验,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如何确认这棵杂树的所有权。他只是隐约的感觉到,如果任由双方斗下去,结果只能是伤人破财,两败俱伤。他想了几个晚上,觉得这棵树是一个祸根,必须要拔掉,关键问题是怎么拔掉?
这位法官当时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有一天,他请原告来到法庭,给原告倒了杯水,试探着问:“这棵树也不值钱,最多十块八块,官司打下去太不值,正好法庭缺少板凳,和你商量一下,能不能给法庭做几张板凳用?”原告一听,这是做好事呀,就说:“既然你找我商量,说明法庭心里有数,这棵树就是我栽的。我听法庭的,把树砍掉。”第二天,他又把被告请到法庭,说了类似的话,并说:“如果树不砍掉,在地头上也耽误庄稼生长。”被告顺水推舟,也乐意原告把树砍掉。就这样,祸根消除了。原告撤回了起诉,此后几年,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没有再发现两家的纠纷。
“但是,”这位法官话题一转,“法庭受理的另外一棵树的案件就产生了问题。”他接着就给我讲了第二棵树的故事。
案子发生在法庭所辖的褚某乡,案情很相似,由法庭另一位法官承办。只不过这棵树是生长在村头池塘边的一棵杨树,原告主张是其所植,但由于其在村子里属于外来户,没有人愿意给其作证。所以原告要求确认杨树归其所有,依据不足。由于调解不成,承办法官最后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一审败诉后,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原告又申请再审,后来,这位法官调离法庭到异地工作。大约是五年后的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那个原告的代理人,询问起原告的情况。代理人惋惜的说:原告已经死了,再也不用打官司了。
“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痛心。我当时就在想,如果这个案件放在我的手里,可能还会照葫芦画瓢,除此确实没有其他好办法。”这位法官叹了口气,顿了顿继续说:“我之所以对这两个案件如此记忆犹新,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个棵树的处理似乎有违法之嫌,但效果很好;第二棵树的处理在法律上或许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生活悲剧。”
这是一个斯芬克斯式的司法谜题!我无奈地宽慰道:“这不是法官的错,这是司法之弊。如何克服司法之弊,这或是法官的永恒课题呢!”
这位资深法官赞许的点点头,继续讲述沉睡在他记忆深处的故事。
三棵树的故事
这是一起排除妨害纠纷。原、被告是隔壁邻居。原告起诉的理由是基于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原告主张,被告在原告房屋的东南角栽了三棵树,已生长数年,严重妨碍了原告农用车的通行,致使其农业生产受到不利影响,据此要求被告排除妨害,将三棵树砍掉。被告则辩称,三棵树均栽种在自家宅基地上,并不侵犯原告的权利,通行问题应由原告自行解决,故不同意砍树。
案件经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三棵树的位置靠近村中的生产路,确实给原告的农用车通行带来不便,从相邻关系处理原则考虑,双方的纠纷应本着团结互助、和睦共处、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处理,故判决被告排除妨害,砍掉栽种在原告房屋东南角的三棵树。被告不服一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庭审结束后,二审合议庭的法官们对案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被告的树木长在自家宅基地里,不存在妨害原告通风、采光和通行问题。原告起诉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担心被告的树木种植在房屋东南方向,影响其风水,但由于风水一说在法律上并无依据,故以妨碍通行为由进行主张。至于通行问题,条条大道通罗马,原告完全有能力另辟蹊径,自己解决,不需要通过限制被告的权利得以实现,故提出改判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主张。但也有人认为,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被告有权在自家的土地上栽树,但该权利的行使应以不妨碍他人的权利为条件。相邻关系处理原则的根本目的系要确立团结、和谐、友善的邻里关系。被告所栽的三棵树虽然并未侵占原告的土地,但客观上给原告的生产通行带来一定不便,故主张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后轮到审判长发言。这位审判长也是一位资深法官。面对合议庭成员针锋相对的观点,他陷入了沉思。经过深思熟虑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村中的生产路是历史形成,村民都有从生产路通行的权利。被告所栽的三棵树虽未侵占原告的土地,但与生产路形成时间相比较为滞后,被告不能以其土地使用权限制原告的生产通行权。鉴于三棵树系成行栽种,每两棵树之间的距离虽不足以农用车通行,但将中间的一棵树伐掉后,预留的空间有四米多宽,已足以解决生产通行问题,故基于相邻关系处理原则,并从利益平衡考虑,应改判将三棵树中的中间一棵伐掉,同时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听了审判长的处理意见,合议庭其他成员纷纷表示赞同。领取判决书的那天,原、被告都笑了,双方之间似乎从未发生过纠纷。
受害人在盗窃电线吗?
树的故事讲完了。这位资深法官还讲述了一个关于触电损害赔偿的案例。
触电损害事故发生在一个深秋的早晨。天刚蒙蒙亮,田里的庄稼上布满了露水。事故现场在一个水沟旁边,岸上是庄稼地,地里有一排电杆,承载着村里1万伏的高压线路。在其中一根电杆上方,缠有一条攀登用的安全带,电杆下方的地面上则散落着钳子以及烧毁的手套等工具,当然还有惨不忍睹的已被高压电分离的肢体……
原告是死者的近亲属,被告是当地的县供电部门。原告起诉的依据是法律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规定。在法律上,高压电属于高度危险作业范畴,除非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否则供电部门难辞其绺。在本案中,供电公司能够免责吗?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事故现场状况,受害人系在盗窃电线过程中遭受高压电电击死亡。根据法律规定,受害人因盗窃电力设施引发的高压电触电事故,电力设施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人已经死了,得不到赔偿不说,还要背着一个“盗窃”的坏名声,这样的诉讼结果显然是原告不能接受的。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一审法院的认定不能说没有道理,根据生活经验和常识,受害人生前确实是在做一件违法的事情。但是这个违法的事情是否一定就是“盗窃”呢?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情吗!但在民事审判程序中,法官是否具有认定某行为构成盗窃的权限呢?这似乎超出了民事审判法官的职权审查范围。但如果不认定为“盗窃”,于情于理都难以自圆其说。
受害人是在盗窃电线吗?如果不是,他究竟在干什么?
上诉审的法官们在绞尽脑汁的思考,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也是原告期待的结果。而在原告看到终审判决书的那刻起,可以肯定的说,原告的负担终于卸下了。终审判决书这样写道:本案损害系由于受害人擅自攀登杆塔造成。擅自攀登杆塔,属于《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禁止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受害人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实施行政法规禁止的行为,电力设施产权人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上诉审的法官们以客观描述的方法化解了一个事实难题。
写给年轻的法官
故事到此结束了,但审判之路还很漫长。
悲剧与喜剧都是人生剧本,并且在生活中不停的发生着辩证的转换。有时他们会被搬上诉讼舞台,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演绎。而这位资深法官所讲述的故事,则是在告诉年轻的法官们,在诉讼舞台上,法官应如何运用其智慧和经验,为法律和生活创作一幕幕喜剧和幽默。
————————
作者|张凯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