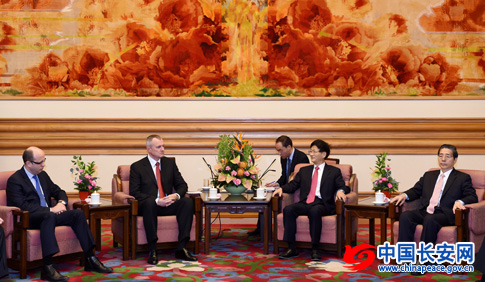图为穗积陈重。 (资料图片)
在我国的学术成果说明中,往往有填补空白之辞,如果这句话套用到翻译界,那么可以说《法窗夜话》也是一项填补空白的翻译。因为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可以在学术史的意义上发现穗积陈重之于中国法学的作用,更能够借以烛照中国百年法律变革的得失。这不是对《法窗夜话》的恭维之词,而是切肤之痛的反思。
法学古董般的存在
穗积陈重在日本法学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他被称为东亚法理学之父,同时又列位日本“民法三杰”;以法学出身,执掌日本学士院。其影响不仅远远超出法学的范畴,而且得到了整个日本学界的承认。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在中国法学的接受史中,穗积陈重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作为法学古董而存在,并没有很好地被纳入到法学史的传承中去,甚至在中国的法理学史中,穗积陈重也仅仅是在提及法理学的译名确定时,被引用一下,而穗积陈重本身所承载的非常丰富的内容则直接被忽略掉。从这个意义上讲,晚清民国时期的法学家反而能够更清楚和更到位地把握穗积陈重对中国法学和法律变革的意义。
所以,回顾中国法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当穗积陈重的代表作《法律进化论》一经出版,很快就被当时的中国法学家翻译引入,并视为经典之作,不能不佩服上世纪二十年代法学译者陶希圣诸人的慧眼。而在近百年之后的当下,《法窗夜话》虽然姗姗来迟,但也是大有裨益。因为《法窗夜话》不仅是《法律进化论》这本未完成巨著的补充之作,也是从侧面让我们充分地认识穗积陈重多层次的法学知识背景构成。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虽然这本夜话百则,没有章节的分类,但是却大体不脱于以下主题:一是法律规则精神的坚信,用今天的主流话语来讲,就是法治精神的宣扬;诸如“帕比尼安拒拟旨”“哈乃斐却职”“商鞅立木为信”等,东西方的法制故事,信手拈来,随意比兴。二是法律进化的呈现,从“贝壳放逐法”“汉谟拉比法典”“格尔蒂石壁法”,到“认妻为母”“动植物之责任”“家界与领海”等等,可以看出法律进化的不同面向和曲折复杂。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
此外,穗积陈重媒介东西方法学。在夜话中,看似对格劳秀斯夫人玛利亚和奥斯丁夫人莎拉的称赞,以及看似颠覆法学史定论地称莱布尼茨为历史法学以及比较法学的鼻祖,其实无不暗含着穗积陈重的法学知识来源。这些知识在穗积陈重翻译定名法理学、准据法等术语名称时候,都发挥着莫大的作用。最后,虽然穗积陈重先生以德国民法典制定中的争论来带出日本民法的编纂,但是毫无疑问,如何在日本法中灌注那种法律的诚信精神以及在日本法的新生中体现法律进化的作用,是穗积陈重先生讲述法律掌故的重心所在。
当然,如果读通了穗积陈重的《法律进化论》,再回头看这本《法窗夜话》,就会发现其条理性更强,完全可以用法律进化的逻辑贯穿其中,并且从中读出:某种类似于黑格尔所讲的“时代精神”体现在日本法的新生之中。这一点,也是尤其需要我们重视的,在日本脱亚入欧的精神运动中,福泽谕吉、穗积陈重这些学人头脑,总会在有意无意之间,以充分包容的心态去容纳东西方文化中比较优秀的成分。我们所熟悉的是流产的“中体西用”,日本却脚踏实地的践行了“和魂洋才”。
所以,在夜话中可以发现,穗积陈重对历史法学、比较法学、分析法学和功利主义等大范围的吸纳和熔铸,以至于在日本民法修订中,作为民法三杰之一的穗积陈重既能够为民法编纂提供总体的精神指导,又能够提供锐利的概念分析工具;同时,在历史法学的意义上为本民族的正当生活论证。抛开法学流派之争,法学史上的穗积陈重真正值得尊重的恰恰在于他不局限于一个具体的流派,而是紧扣日本法新生的现实从容出入于各种法学体系。
打开法理学视界
全面地认识穗积陈重在法学史上的位置,能够让我们明了法学家、法学流派对于法学和本民族立法的意义。首先就狭义的法理学而言,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全面追踪国际法哲学界的前沿理论,也不仅仅是面对当下中国法律事件的即时性分析,或许打通历史的环节会让我们的视野更为开阔、更能够找到事件和研究问题的意义连接点。在这一点上,中国法制史、民法乃至刑法做得都不错,当然做得最好的乃是法制史领域,因为可以看到仁井田陞、滋贺秀三等人的研究,已经被纳入到中国法制史当下的研究传统中去了。
如果在法理学的范围内,把穗积陈重的探索和努力纳入进去,至少我们可以不再轻易地重提法学的流派之争,而是能够看到如何熔铸不同的法学流派去回应中国的法律实践。就此而言,中国法理学或法学领域的实践并非是一篇空白,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陶希圣诸公在翻译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前后就已经意识到融合西方法学流派来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重要性,所以陶希圣通过吸收历史法学之梅因和法律社会学之埃尔利希、庞德等人的研究方法,率先提出了法律的社会史研究。由此,反观当下中国法理学乃至法学领域的诸多研究,虽然有历史法学的重提以及对法学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多方面的研究,但似乎仍然缺少一种法学史的贯通,因为这些研究并不是绝对排斥分析法学。
经由贯通,打开法理学的视界,那么法理学介入当下民法典的编纂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总体性的存在,本身就不是孤悬诸分支法学之外的。当我们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法理学家或法哲学家举例证成法理学家不是单纯的法理学家时,我们依然忘记了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沐浴此过程的日本法理学者和早期中国的法理学者,都是以包容的心态容纳各个法学流派,自由地出入法学主要学科的。所以,无论是在德国的民法典制定过程中,还是日本的民法典制定过程中,法理学者都是天然正当的参与者乃至主导者。
一本书有多重读法,如果无意于纠结穗积陈重在法学史上的地位,或者穗积陈重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那么,完全可以把《法窗夜话》作为一册法律史话,一位亲历法学及其实践的智慧老者,与你趣谈法律,驱赶你研习法律的枯燥。诚如斯言“倘若人生并非索然无味,则法律故事亦如是”。(白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