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策:用手中的笔展现警察人生的命运之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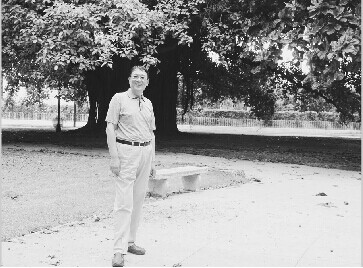
和温文尔雅的张策相处,你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如沐春风。他那很有些文人气息的真性情,要读他的文字才能感受到。
“误入官场”
由于工作关系,和张策打了近10年交道,第一次留下深刻印象,便是通过他的文字。
认识张策不久,他出了本新书——小说自选集《刑警队》。他送我一本。拿到书,我习惯性地从后往前翻,看的第一篇便是他写的后记,还没看几行便忍不住乐了。
这后记的第一句话是“我曾是个误入官场的人”。而后讲述了他当年“误入官场”的故事。
这被他“误入”的官场是N年前的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副处长位置。这个位置,张策本来并没啥兴趣。他天性散淡,人生乐趣和精神寄托都在写作上,组织上有意提拔他当这个副处长,被他婉言谢绝。结果当时的处长对他说:难道你愿意让某某来领导你吗?这让他无言以对。虽然想象不出被某某领导会是啥滋味,但想想被任何人领导也不如领导别人舒服吧?算明白了这笔账,遂糊里糊涂当了这个副处长。
因为不愿意被领导而走上某个岗位去领导别人,这种事在官场虽非绝无仅有,却也不常见到。这听上去很像是悖论,实际上类似的事情我们人生中不免常会遇到。我们常常被情势所迫不得不去做某个选择,看上去是我们在选择,实际上主动权和决定权都不在我们手中。所谓的“误入”,说穿了只不过是命运的播弄,在这个意义上,命运犹如刀俎,我们都只是鱼肉。
张策检讨了在这件事上自己的“贪婪”和“自私”,批评自己“不愿意被人管着,还有点儿想管别人的意思”。而在我看来,这件事儿折射出的恰是他身上可贵的文人气质:狷介、清高、孤傲,对官场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与人品才华多半无关的等级关系发自内心的抵触;以及面对命运的强势时某种软弱和被动。
最近,为了写这篇报道去采访张策,我又听说了他生命中的另一次“误入”故事。而那次“误入”比这次更富戏剧性。
人生谷底
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儿。1976年,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那年,张策也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桩大事:他高中毕业,由于学习成绩及各方面表现还算突出,和一位同学一起被推荐给了来校招人的国务院某机关人事部门。招工人员的满面严肃,意味着他们将成为“国务院的人”。那年月,高考尚未恢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仍在继续,大多数城市高中毕业生的出路,要么是下农村,要么是去工厂,能够去这样的大机关工作简直是烧了高香。张策一夜间成了幸运儿,走到哪都会迎来同龄人艳羡的目光。
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国务院招工人员嘴里的“单位”层层下降:先是变成了文物事业管理局,然后又到了下属单位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根据工作需要,又将他们分配到行政处。到最后,张策成为一名水暖工,那位同学则干了瓦工。于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毕业生成了成天和故宫大院里包括男女厕所在内的水暖管道打交道的人。
那个年代,许多人在某个工作岗位上一呆就可能是一辈子。谁也不敢保证,这份水暖维修工的职业不会是张策一辈子的归宿,无论他有多不甘心。
那段经历在张策的记忆中大体是这样的:“总背着一只厕所的白瓷便器,像只白壳乌龟似的,四处乱走。”平时,无论哪里的水管堵了,他们得随叫随到;如果堵的地方是女厕所,进去前须先大吼一声,确定没人才能抬脚。冬天的棉大衣只配备到某级别以上工作人员,长年露天作业的水暖工只能穿别人换新时淘汰下来的旧棉大衣……
活儿脏累也罢了,那种低人一等、不被尊重的屈辱感至今回忆起来“依旧可以刺痛灵魂”。
这场“误入事件”持续了3年。3年后张策被调入北京市公安局,成为一名拿笔杆子的宣传民警,他的人生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篇章。如今担任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拥有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等诸多身份的张策对这段生活更多的是感谢,是这段始料未及的人生谷底经历,令他初次领略到了命运的诡谲与莫测,让他养成了思考的习惯;也正是这段生活培养了他“向下”的眼界和关注底层生活的写作方向。3年的底层生活经历,给他的人生及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上了一层淳厚的底色。
两部新作
就在采访张策前几天,传来消息,张策的两部新作,中篇小说《命运之魅》和《青花瓷》被推荐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刚巧,这两部小说我刚刚读完。
两部新作分别发表于2013年的《啄木鸟》和《十月》,又分别于今年被《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选登。和张策以往的作品相比较,它们叙事更为纯熟、语言更为老到,而无论是叙事手法还是语言风格,都有许多创新;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则与他的旧作一脉相承,那就是对人性和命运的深刻思考。
《青花瓷》描写一位前军阀姨太太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嫁入刘姓人家后,与刘家两代人在几十年间的坎坷遭际,以历史的风雨为背景,凸现出人性在无常的命运面前的坚韧与悲凉。女主人公冯婉如那虽强悍却终脆弱的生命一如文中那几尊价值连城却未被人识、难得善终的青花瓷,令人感叹心酸。这是部非公安题材作品,它让我们多少窥见了张策的创作野心和今后的创作走向。
这里想重点说说《命运之魅》。这部小说如同张策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写的是警察,展现的是警察这份职业给身在其中的个体生命打下的烙印以及对其命运的深刻影响。它在许多文学手法上令人想起张策多年前的知名之作《无悔追踪》,而故事更为丰满、内涵更为深厚。
《命运之魅》也像《无悔追踪》一样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故事中的“我”是位刚跨出校门不久、初尝公安生活滋味的80后女警。一个偶然机会,“我”得知自己家族上溯五代竟然全部是警察。在对警察祖先的历史进行挖掘梳理时,“我”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我”的祖爷爷,一位中共烈士,很可能牺牲于同一所警官学校毕业的异母兄长的出卖。被历史尘封的事情真相在随后的叙事中被一步步揭开:“我”的判断是对的,祖爷爷的确由于兄长告发而牺牲。而名叫陈郁的那位兄长告发弟弟是奉上级组织指示行事,目的是掩护自己的地下党卧底身份,以完成一个重要任务。在得知弟弟牺牲的消息后,陈郁一夜间白了头发。但他什么也没说,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默默地关照着弟弟的家人,并继续执行自己的卧底任务,孤独终生。
忠实履职,为之不惜牺牲全部人生甚至亲人的性命,地下党卧底陈郁和《无悔追踪》中的警察老肖,走的是一条多么相似的命运之路。小说的叙事手法也和《无悔追踪》相近,采用双线叙事,历史和现实相互穿插,两个不同时空里发生的故事交递推进,对家族历史的叙述,常常大胆地以“我”脑海里的想象为展开主线,辅以现实中真实资料的印证和补充。
这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无悔追踪》集中全部笔墨描写警察老肖追踪特务冯静波几十年的执著与坚韧,讲述了一个个人英雄式故事;《命运之魅》则在浓墨重彩叙述陈郁、陈郑兄弟传奇故事的同时,还展现了“我”的家族五代人中另外几位警察坚守职责、牺牲奉献的人生故事,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忠于职守的警察,是英雄群像,虽然限于中篇的容量,这群警察的面目稍显模糊。小说结尾,更是以本已对平淡无奇的公安生活心生厌倦的“我”的回归警队,寓意新时期人民警察职业精神在年轻一代身上的传承。
双重缘分
张策曾在某部小说的自序中说:“从没有任何职业会如此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会如此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爱好以至全部生活。不要以为只有刀光剑影、生死瞬间才是警察所面对的考验,更大的考验或者说对于更多普通警察的考验是生活和工作的错位,是工作对个人生活的毫不留情的侵入和改变。”
在生活和工作的错位中,在因此而常常难以避免的坎坷际遇中,依然葆有初心,坚守职业信念,忠实履行职责;以足堪洞穿沉重历史和无常命运的人性之光,璀璨着这份职业的神圣与荣耀,这便是张策多年来着意塑造的英雄警察形象。这样的警察形象,不只出现在《无悔追踪》和《命运之魅》中,也出现在他的“无”字系列中篇小说、《刑警队》中篇小说集及其他警察题材作品中。
张策为《命运之魅》写过一篇后记,题目是“命运:永远的文学主题”。张策出身公安世家,父母双双为北京市公安局离休警官。成为以警察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作家,用手中的笔去探索、解析警察职业和警察人生的奥妙,似乎是他天定的命运。这样的写作,是他和文学、和警察职业的双重缘分,也是他生命中的“命运之魅”。
(记者 丁晓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