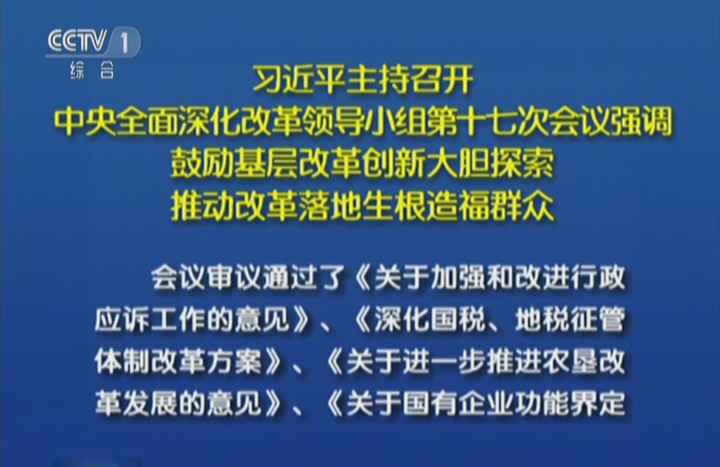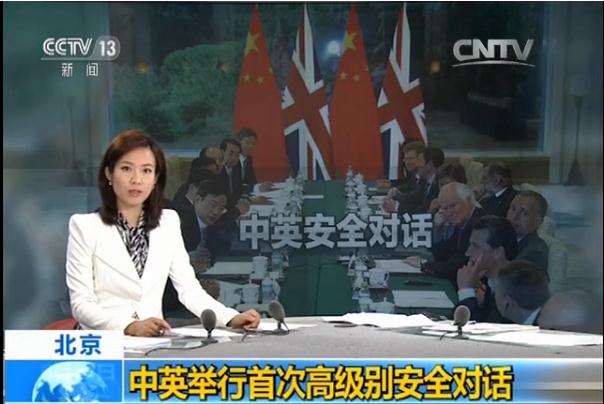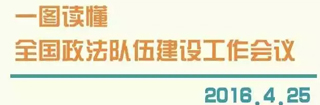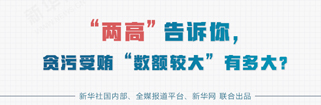从“杨志杀牛二”看唐宋时的“斗殴杀人”
《水浒》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中提到,“青面兽”杨志沦落到在汴京城售卖自己祖上传下来的宝刀,结果遭遇京师有名的地痞牛二。牛二对杨志百般纠缠挑衅,原文记载:
牛二紧揪住杨志说道:“我偏要买你这口刀。”杨志道:“你要买,将钱来。”
牛二道:“我没钱。”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这口刀。”杨志道:“我不与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杨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跤。牛二爬将起来,钻入杨志怀里。杨志叫道:“街坊邻舍,都是证见:杨志无盘缠,自卖这口刀,这个泼皮强夺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这牛二,谁敢向前来劝。牛二喝道:“你说我打你,便打杀直甚么?”口里说,一面挥起右手一拳打来,杨志霍地躲过,拿着刀抢入来,一时性起,望牛二嗓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杨志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随后,杨志去开封府自首,府尹非常同情杨志,于是做了这样的认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不难看出,在处理这起“落魄英雄怒杀地痞”的案件中,府尹的处理耐人寻味。
自汉代开始,对于杀人罪的“谋杀”、“斗杀”、“戏杀”、“狂易杀人”、“轻侮杀人”等不同情节,已经给予不同处罚,而到了唐代,更是在《斗讼律》中将杀人罪类型化为六类,即“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其中,“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虽无事先预谋,但在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意愿,即“冲动型杀人”;“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戏杀”、“过失杀”均指因各种原因的过失而导致他人死亡。在责任承担上,谋杀、故杀处罚较重,而斗杀、误杀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戏杀则减斗杀罪二等处罚,过失杀则允许以金钱抵罪。唐代关于“六杀”的划分和处罚原则基本上为宋代所继承。
正因为“斗杀”刑事责任较轻,所以《水浒》中有不少司法官员为了保全杀人者而更改罪名的例子。例如,在第二十六回“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中,武松为了报兄长之仇,持刀袭杀了西门庆,嗣后割下仇人头颅祭拜兄长。从整件事观察,武松显然属于有预谋的“谋杀”,但司法官员感念武松的“忠义”,有心保全,遂将其罪名由“谋杀”更改为“斗杀”,大大减轻了其刑事责任,最后只需要“刺配充军”而无需抵命。
必须指出,无论是“杨志杀牛二”,还是“武松复仇”,即使司法官员将他们认定为“斗杀”,按照宋代的法律,也是要被判处死刑的。《宋刑统》中规定,“诸斗殴杀人者,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因此,即使将杨志和武松认定为“斗殴杀人”,但由于二人均在斗殴中使用了兵刃,因此在处罚上“与故杀同”。因此,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依照当时的法律二人难逃一死。
时至今日,“六杀”的区分已经成为历史。在现代刑法中,值得关注的是犯罪人持械致人死亡的案件究竟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还是故意杀人罪的问题。一般而言,需要从两个层面考虑:
其一,主观层面有无杀人的目的、动机和故意。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侦查机关在圈定犯罪嫌疑人时,非常注重调查受害人平时的人际关系和社交圈,从而大致判断受害人是死于“财杀”、“情杀”还是“仇杀”,这对于明确犯罪动机从而锁定最终的犯罪嫌疑人非常重要。不难看出,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是犯罪活动的初始心理因素,它统领着犯罪活动过程的全过程,贯穿犯罪始终,并在犯罪进程中给犯罪人提供持续的心理支持。但是,考察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的目的仍然在于把握犯罪故意。这是因为,尽管实践中“没有无缘无故的杀人”,但的确存在一些杀人动机很弱甚至缺乏具体目的的杀人行为,因此,根据各种主客观情节综合判断、推定杀人者的主观故意内容,是主观层面的主要分析内容。
例如,武松杀西门庆有足够的杀人动机(为兄复仇),而其杀人后的行为(割首祭兄),也证实了其是杀害的故意而非伤害的故意。又如,在杨志杀牛二的过程中,在起始阶段我们难以判断杨志是动了杀机还是仅仅想教训一下杨志,但是看到后面,牛二倒地后,杨志仍然“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显然,结合补刀行为可以毫无疑义地判定其主观上就是为了追求牛二死亡结果的发生。
其二,客观层面使用的工具和打击的部位。
人的主观心理活动事实上是无法观察的,但人们可以从客观行为和事实进行捕捉和推定。首先,如果犯罪人使用的是危险程度较高的凶器,则可以推定其具有较高的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正因为这个原因,唐律和宋律均推定持刃斗殴致人死亡的,按故意杀人罪处罚。时至今日,考察犯罪人所使用的犯罪工具仍然是我们定性的重要依据。其次,犯罪人对受害人的打击部位,同样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其主观意志。在武松和杨志杀人过程中,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点。例如,杨志杀牛二过程的最后是“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显然,用削铁如泥的宝刀在胸脯上连戳两刀,在致命部位造成贯通伤,其主观目的显而易见。(袁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