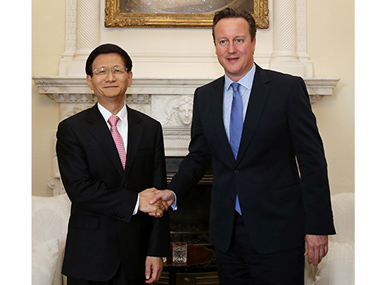聚散两依依
2003年底一个傍晚,离家近1年的我回到厦门,走进小区远远就听见人们的欢声笑语。人群中,我和妻子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妻子拉着3岁女儿笑吟吟地走向我,不时低头提醒:“快看,快看,这是谁?”
女儿吸吮着手指怯怯地躲在妻子身后,鼓足勇气叫了我一声:“叔叔好!”
周边一阵大笑,我心酸地抱起女儿,顾不得她哇哇大哭,连声提醒:“我是你老爸!”
2002年,妻子舍弃老家悠闲的工作随军落户厦门,而我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应急救援部队,常年在全国各地执行任务,原以为从此相依相偎,但之后9年里我们实际相聚时间不到12个月。在无数个离别的日子里,厦门,还有在这美丽之岛的家,成了我在无数个星月当空的夜里最温馨的记忆。
孩子上幼儿园不久,妻子参加招聘考试被街道办录用。从那以后,她除了忙于繁杂的工作,就是围着女儿打转,每天下班忙完所有家务都已是午夜。我们每次电话内容大多只有简单几句:“睡了吗?”“准备睡了”“家里怎样?”“挺好的,你自己在外多保重!”
某天,妻子在电话里说出了一个她的想法:“我想入党,你看我具备条件吗?”我呵呵一笑:“你一个家庭妇女还真有追求啊!”原以为这不过是她的玩笑话,某次探亲回家,妻子拿出一本通红的《党员证》在我眼前晃动,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几乎是我们婚后她最动人的笑。
在那之后的6年,妻子利用极为有限的休息时间参加了函授学习,先后拿到了大专、本科学历……
当初,妻子在极度艰辛劳累的条件下坚持要求入党、夜以继日参加函授学习时,我承认我曾报以一种玩笑、甚至不屑一顾的态度。而当妻子完成了所有这一切我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后,我才醒悟自己当初的无知和浅薄,继而对她生出深深的敬重。
2007年春节,我随部队移驻河南,那年的春节全家相聚在大雪封山的太行山脚下,6岁的女儿就像刻在我身上的一枚符号般如影随形。7天相聚,随之便是近一年的别离。那个深夜,我把妻女送上南归的列车,列车即将开动那一瞬,站台上的我突然发现女儿的小脸紧贴车窗,脸上挂着两行晶莹的泪,一言不发地看着我。那一刻让我彻底领略到了心碎的别离,也烙成了我对聚散依依最刻骨铭心的印记。
2011年底,服役23年的我转业安置在岛外一个偏远派出所。自此,平素节俭的妻子总喜欢把客厅吊灯开到最亮的那一档,我揶揄地笑问:“怎么,不怕浪费电?” 妻子嗔笑:“开亮一点,让我感觉到你是真实的……”我心中顿时满怀愧疚。
事实上,在派出所工作这些年,全家相聚的时光并没有增加多少,但我和妻子却在平凡的家庭生活中达成了某种默契:晚上赶回家吃完妻子做好的晚饭,我就接手洗碗拖地;女儿在她那小房间忙着似乎永远都做不完的功课,妻子总会躺在沙发上小憩片刻。偶尔我们会对望一眼,我只想让妻子知道,无论聚散,我都是真实的我,她也是真实的她,我们从来没有过分离。(罗晓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