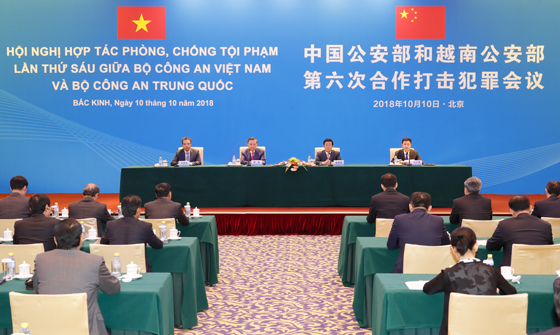又到一年重阳节。
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视该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上海以14.3%的比例,成为我国常住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而作为中心城区的长宁区,已提前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每个老人的今天都是我们的明天。
面对一个个年老体弱却因种种原因来到法院的当事人,如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每一位老人都能优雅地老去,是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的法官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精神赡养,是否已被忽视太久
“我身体不好,自己的养老金刚刚够用,还要请人打扫、做饭,要她每个月给我1000元的赡养费又不过分!”75岁的梁老先生越说越委屈,“她这两年来家里看我的次数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去年我做手术开刀时,她也故意不来……”
梁老先生口中的“她”其实是女儿梁静。多年前,梁老先生与妻子离婚,后虽有再婚但并未再有子女,年纪大了,这个唯一的女儿就成了他最牵挂的人。然而,由于两代人在生活和思维习惯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善沟通造成的种种误解,这对父女的关系在最近两年持续恶化——在父亲眼里,曾经常带他外出旅游、吃饭的女儿对自己越来越不耐烦,仅仅在中秋、冬至这些节日才走过场似的来家里看看,态度也是冷冰冰的;而在女儿梁静看来,父亲性格固执,脾气火爆,强行干涉自己的感情生活,还一度在公共场合教训自己,让她十分反感。
于是,难以忍受女儿长期漠视的梁老先生把女儿告上法庭,除了每月1000元的赡养费诉请,还要求女儿每周至少来看望自己一次。
“其实原告梁老先生自身条件并不差,他也承认,相对于那1000元的赡养费,更希望女儿能常回家看看,陪自己说说话。”负责该案件的耿志成法官说,“老人觉得女儿躲他,就认为:‘那就法庭见!法官通知开庭时,你总不能还躲着不见我吧?’”
案件审理过程中,女儿梁静坦言,过去两年因各种原因父女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自己确实减少了探望次数,对父亲关心不够。但自己每周末需要上课、看病,每周看望一次的要求实在难以满足。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赡养父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相关涉老法律同样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有义务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这也被媒体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
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精神赡养的真正实现不能仅靠法院的一纸判决,更重要的是两代人放下成见、友好沟通和相互理解。最终,综合双方当事人的具体情况,法院驳回了梁老先生要求女儿每月给付其赡养费1000元的诉讼请求,但要求梁静每月至少看望梁老先生一次。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八旬老太,为何与孙辈争遗产
年过八旬的金阿姨多年前老伴因公殉职,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将儿子养育成人,儿子陈斌结婚生子且有不错的工作和收入。本该安享晚年的她却不曾想到儿子因一场车祸意外去世,自己独自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更让金阿姨难以接受的是,与自己相处融洽、在处理儿子后事时也并未有任何反常的儿媳突然拿出一份遗嘱,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本人生前全部财产归女儿陈小雪所有。”落款处还有儿子的亲笔签名,日期则是出意外身亡的前几天。
金阿姨实在想不通,儿子是意外身亡,怎么会在出事前几天留下这只有一句话的遗嘱?最后,金阿姨顶着巨大压力将儿媳和孙女诉至法院,要求按法律规定继承儿子遗产中属于自己的应有份额。
陈斌生前曾是上海某大型企业的高管,收入较高,属于遗产部分的房产、证券、现金等价值1000万元左右。法庭首先对这份略显蹊跷的遗嘱委托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而鉴定结果却让金阿姨大跌眼镜——这份遗嘱确实是由儿子陈斌本人书写!
遗嘱真实有效,那么是否意味着自己一分钱都拿不到?这对于年老多病、只有一套自住房屋的金阿姨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我国继承法第十九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法官在充分了解当事人生活状况后,本着在法律框架内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判决陈斌遗产中的30万元由金阿姨继承,其余按照遗嘱由陈斌的女儿陈小雪继承。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斯人已逝,她的遗愿谁来守护
“耿老师,这个遗嘱继承案子的当事人和去世的老太太您应该还有印象的。”书记员温馨提醒法官耿志成,“几年之前因为被侵吞了90多万元的房屋补偿款,这个刘老太把儿子告了,但是判决下来儿子只还了8万元,没过两年老太太就走了。”
耿志成找出几年前那起分家析产纠纷案件的材料,很快回想起了那个年近九十还颤颤巍巍地来到法院立案的刘老太和她口中的“不孝子”大李。
5年前,刘老太一家的公房因市区旧改项目被动迁安置,刘老太因腿脚不便委托儿子大李与相关部门签订了协议并取得了270余万元的安置款。而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大李分多次将这笔钱转至自己和案外人秦某名下。法庭调查后发现,大李和妻子正是在这段时间买下了秦某的两处房产,分别登记在大李夫妇和儿子小李名下,房产转让价款共200万元。
公房内原有刘老太、儿子大李和孙子小李三人的户籍,关于本应属于母亲的90余万元安置款,儿子大李总是在“打太极”:一会说和母亲商量过,根据母亲意思已经用完了;一会又说新房精心装修过,给母亲保留了最好的房间……刘老太的态度则很明确,“我就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动迁款!”
最终,法院支持刘老太的诉请,判决大李夫妇及儿子三人共同偿付刘老太90余万元。
“后来刘老太住到了女儿家里,生病后由两个女儿分别照顾。这次的争议焦点还是在大李一家尚未偿还的80多万元补偿款,不过两边都拿出了遗嘱。”对处理了上百起继承案件的资深法官耿志成来说,显然并不意外。
原告方刘老太的两个女儿提供的遗嘱明确显示,“生病后全靠女儿照顾,属于我的那份动迁款除去看病等的钱,全部由两女儿继承。”落款时间是刘老太去世前一年左右。而在被告大李提供的遗嘱中,刘老太竟表示自己“从来不想去法院告我儿子和孙子”,自己的动迁份额也“全部赠与孙子小李”,落款时间也晚于前者,为刘老太去世三天前。
在对两份相矛盾的遗嘱进行鉴定后,鉴定中心以字迹特征不稳定和指纹线模糊为由表示无法出具鉴定意见,双方也未提出指定其他机构进行鉴定。“两个女儿提供的遗嘱和刘老太生前一贯意思表示一致,因为她住院前还上过电视台的谈话节目,曾公开表示将把遗产留给女儿们继承。而被告提供的遗嘱除了与死者生前表示相矛盾外,还有很多疑点。”耿志成补充说,“我们专门查了刘老太当时的病历,发现她去世前几天精神状况基本都是神志欠清,旁边病床的病人也证实大李从未带人看过刘老太。”
最后,法院认定刘老太两个女儿提供的遗嘱合法有效,各继承刘老太生前债权的50%,即儿子大李一家需向两个姐姐偿付80余万元债务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利息。
“这也算是帮助老人完成一份遗愿吧,希望她能走得安心。”耿志成法官最后这样说道。(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评论:司法“护老”需尊重老人真实意思人们常说,“最美不过夕阳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幸福养老”“优雅老去”也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出台与修订凸显了对老年人的倾斜保护,而立法“护老”后更需要司法“护老”的保驾护航。老年人的权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障,是衡量人口老龄化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近三年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每年审理涉老纠纷案件均在2500件以上,且呈逐年上升态势,主要类型包括继承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离婚及离婚后财产纠纷及赡养纠纷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众多关系到老年人切身利益的家事案件中,老年人因为其生理、心理特点在诉讼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沦为子女利益争夺大战中被利用的一方,自身意志得不到相应的尊重和维护。
“一些赡养费纠纷和继承案件,其实是子女间的矛盾,但常常以老人的名义提起诉讼。这反映出一些老年人‘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于是经常‘被原告’‘被维权’。”耿志成法官说。
而除了“不敢”,还有相当一大部分老年人则是“不会”维权。许多老年人缺乏相关法律知识,维权意识和能力均有待增强,特别是收集和保留证据的意识较弱,在诉讼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另外,还有一些老年人‘过度维权’,比如像梁老先生这样通过‘闹到法院’引起小辈的注意,意在惩罚子女对自己的忽视。”
针对这些问题,长宁法院一方面继续抓牢涉老纠纷审判主线,通过“审判力量到位、法律释明到位、事实调查到位、调解工作到位、便利保障到位”全面提升审判质效;另一方面,以“治未病”的理念,通过“内容全方位”和“地域全覆盖”开展老年人权益保障宣讲活动,走进社区、走近家门,提升老年人的法制意识,在强化矛盾源头治理的同时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推动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
“家庭纠纷往往具有很强的牵连性,数起案件,看似不同案由,实则只有一点。”耿志成总结,“所以我们在准备宣讲内容时,不局限于一类案件,而是由案件引申出背后的家庭沟通模式和矛盾防患意识。”
法、理、情,一个都不能少。法官们在审判和普法工作之外,还与长宁区“爱晚亭”敬老院结成对子,除了慰问、谈心和物品赠送等“常规”帮扶工作,八年来还帮助养老院解决搬家、内部纠纷协调等困难,而每年春节前夕的“大联欢”也成为法院干警与老人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2016年,长宁法院民四庭(原家事案件审判庭)被全国老龄办、最高人民法院等联合评选为“全国老年法律维权工作先进集体”。如今,站在家事审判改革的新起点上,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家事纠纷多元调解机制,依法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力促在全社会形成“尊老、敬老、爱老、护老”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