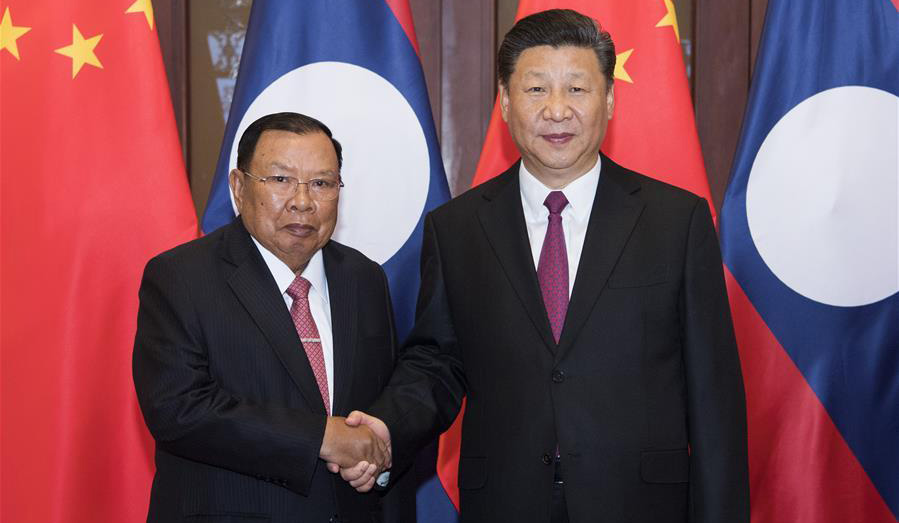第七章 威胁信息
印春荣叹了口气,鲁迈的悲剧,让他心情沉重了起来。
第一次见到“上帝之眼”图案的时候,印春荣其实并没有在意,但接二连三地发现印有这个图案的毒品包装纸以后,他才感觉这个图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贩毒集团的标志,为首的便是大毒枭裘天。
印春荣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加了这样一个好友,但是一看到“上帝之眼”的图案,印春荣不由得警觉起来,或许这已经成了他的职业病了。
打开与“上帝之眼”的聊天记录,那是一段语音。
“三哥,恭喜你!希望你就此打住,否则你知道后果!”
印春荣反复听着这段语音,“三哥”是印春荣卧底时毒贩对他的称呼,后来有的战友也会叫他三哥,但从内容来看,发来这段语言的不可能是战友,也不像恶作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毒贩发出的威胁信息。
威胁信息印春荣也时有收到,曾经有毒贩开出100万人民币的价码买他的人头。
每当收到这样的威胁信息,印春荣心里其实还是很不踏实的,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只是担心那些穷凶极恶的毒贩把怒气发到自己家人身上。
印春荣知道毒品的危害有多大,一千克高纯度的海洛因会引发两千多起刑事案件。在边境,多缴一克毒品,就会减少一分危害。缉毒关系着国家兴亡、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只要他还穿着军装,头顶着国徽,肩上扛着责任,他就不会害怕,更不会退缩。
反复听了几遍以后,印春荣依旧辨不出这个声音,只得给“上帝之眼”回复了几个字:“你是谁?”
消息发过去以后,对方再没有任何回应,但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上帝之眼”图案突然出现,意味着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这么多年与毒贩的博弈,印春荣渐渐占据了上风,对毒贩贩毒的手段可谓了如指掌,他已成为一把利剑,让毒贩闻风丧胆。
毒贩一般行事谨慎,不会轻易露面,他们狡猾得好像一只只狐狸,这一次冒失地给印春荣发信息,表面上是一种挑衅,实则是一种心虚。他们知道,只要有印春荣在,他们“出货”就不会那样简单。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于印春荣来说,自从走上缉毒之路以后,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要还有毒品,他的脚步就一天不会停歇。
“上帝之眼”原本是裘天独有的标志,这次出现,极有可能是裘天的贩毒集团又死灰复燃了。
印春荣盯着微信,思绪翻滚。
想起第一次与裘天交手,那应该是十五年前了,那时的印春荣还是保山边防支队副参谋长,分管情报和缉毒工作。
2002年8月,印春荣截获这样一条通话线索——“天哥,老周已到阿昆家,大电视机可以看,效果很好。”
印春荣反复推敲这句话,根据经验,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天哥,广州人已经到了昆明,大货车已经准备好,非常隐蔽,可以出货。”
破译了毒贩的暗语后,印春荣断定毒贩近期可能有大动作,用大货车运毒,一般都是大手笔。
“排查一切可疑的大货车。”印春荣向二线边境检查站交代道。
八月的滇西,曼海桥依旧异常炎热,火辣辣的太阳像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似要散发全部热量,花草树木都显得无精打采,黏糊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人们恨不得钻到冰箱里。
曼海桥公安边境检查站的边防官兵全副武装,穿着近十斤的防弹衣,戴着又重又硬的防弹头盔。在室外,即便不动,热汗也止不住地流。
印春荣一边擦着汗,一边指挥着执勤官兵留意过往的车辆,尤其是大货车。
在截获情报以后,印春荣带着一名情报科侦查员赶到曼海桥边境检查站,与官兵一起参与查缉工作。
已经过了三天了,查了无数辆车,依旧没有发现毒贩口中的那台“大电视机”。
技侦那边也没有发现那个电话再打过,线索好像消失了。
“印副,我估计是毒贩故布迷阵,我们在这里这样查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情报科侦查员杜风脱下了防弹头盔,对印春荣说道。
印春荣笑笑:“缉毒嘛,就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应该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不要轻易放过每一条线索。毒贩在暗,我们在明,抓住他确实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在众多的大货车中,要找到那辆运毒车谈何容易。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货物都翻一遍,或许那辆车早已经从我们身边过去了,又或许它从其他路线走了。”杜风愤愤地说道,连日来的查缉让他有些急躁。
印春荣无法回答杜风的问题。杜风分析得也有道理,公开查缉本来就有它自身的缺陷,如果没有情报作为先导,要想通过人力把过往的一辆又一辆大货车都细细检查,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都说人有第六感。
虽然印春荣不否认杜风的观点,但是他总感觉,那辆运毒车还没有从自己身边经过,而且肯定会走曼海桥这条线。
光凭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知道是说服不了别人的,就连自己也说服不了。印春荣只能期盼技侦那边能有新的线索,也希望那辆运毒车能够经过自己的身旁。
印春荣叹了口气,鲁迈的悲剧,让他心情沉重了起来。
第一次见到“上帝之眼”图案的时候,印春荣其实并没有在意,但接二连三地发现印有这个图案的毒品包装纸以后,他才感觉这个图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贩毒集团的标志,为首的便是大毒枭裘天。
印春荣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加了这样一个好友,但是一看到“上帝之眼”的图案,印春荣不由得警觉起来,或许这已经成了他的职业病了。
打开与“上帝之眼”的聊天记录,那是一段语音。
“三哥,恭喜你!希望你就此打住,否则你知道后果!”
印春荣反复听着这段语音,“三哥”是印春荣卧底时毒贩对他的称呼,后来有的战友也会叫他三哥,但从内容来看,发来这段语言的不可能是战友,也不像恶作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毒贩发出的威胁信息。
威胁信息印春荣也时有收到,曾经有毒贩开出100万人民币的价码买他的人头。
每当收到这样的威胁信息,印春荣心里其实还是很不踏实的,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只是担心那些穷凶极恶的毒贩把怒气发到自己家人身上。
印春荣知道毒品的危害有多大,一千克高纯度的海洛因会引发两千多起刑事案件。在边境,多缴一克毒品,就会减少一分危害。缉毒关系着国家兴亡、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只要他还穿着军装,头顶着国徽,肩上扛着责任,他就不会害怕,更不会退缩。
反复听了几遍以后,印春荣依旧辨不出这个声音,只得给“上帝之眼”回复了几个字:“你是谁?”
消息发过去以后,对方再没有任何回应,但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上帝之眼”图案突然出现,意味着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这么多年与毒贩的博弈,印春荣渐渐占据了上风,对毒贩贩毒的手段可谓了如指掌,他已成为一把利剑,让毒贩闻风丧胆。
毒贩一般行事谨慎,不会轻易露面,他们狡猾得好像一只只狐狸,这一次冒失地给印春荣发信息,表面上是一种挑衅,实则是一种心虚。他们知道,只要有印春荣在,他们“出货”就不会那样简单。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对于印春荣来说,自从走上缉毒之路以后,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要还有毒品,他的脚步就一天不会停歇。
“上帝之眼”原本是裘天独有的标志,这次出现,极有可能是裘天的贩毒集团又死灰复燃了。
印春荣盯着微信,思绪翻滚。
想起第一次与裘天交手,那应该是十五年前了,那时的印春荣还是保山边防支队副参谋长,分管情报和缉毒工作。
2002年8月,印春荣截获这样一条通话线索——“天哥,老周已到阿昆家,大电视机可以看,效果很好。”
印春荣反复推敲这句话,根据经验,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天哥,广州人已经到了昆明,大货车已经准备好,非常隐蔽,可以出货。”
破译了毒贩的暗语后,印春荣断定毒贩近期可能有大动作,用大货车运毒,一般都是大手笔。
“排查一切可疑的大货车。”印春荣向二线边境检查站交代道。
八月的滇西,曼海桥依旧异常炎热,火辣辣的太阳像个大火球,炙烤着大地,似要散发全部热量,花草树木都显得无精打采,黏糊糊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人们恨不得钻到冰箱里。
曼海桥公安边境检查站的边防官兵全副武装,穿着近十斤的防弹衣,戴着又重又硬的防弹头盔。在室外,即便不动,热汗也止不住地流。
印春荣一边擦着汗,一边指挥着执勤官兵留意过往的车辆,尤其是大货车。
在截获情报以后,印春荣带着一名情报科侦查员赶到曼海桥边境检查站,与官兵一起参与查缉工作。
已经过了三天了,查了无数辆车,依旧没有发现毒贩口中的那台“大电视机”。
技侦那边也没有发现那个电话再打过,线索好像消失了。
“印副,我估计是毒贩故布迷阵,我们在这里这样查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情报科侦查员杜风脱下了防弹头盔,对印春荣说道。
印春荣笑笑:“缉毒嘛,就是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应该做百分之百的努力,不要轻易放过每一条线索。毒贩在暗,我们在明,抓住他确实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在众多的大货车中,要找到那辆运毒车谈何容易。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货物都翻一遍,或许那辆车早已经从我们身边过去了,又或许它从其他路线走了。”杜风愤愤地说道,连日来的查缉让他有些急躁。
印春荣无法回答杜风的问题。杜风分析得也有道理,公开查缉本来就有它自身的缺陷,如果没有情报作为先导,要想通过人力把过往的一辆又一辆大货车都细细检查,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都说人有第六感。
虽然印春荣不否认杜风的观点,但是他总感觉,那辆运毒车还没有从自己身边经过,而且肯定会走曼海桥这条线。
光凭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知道是说服不了别人的,就连自己也说服不了。印春荣只能期盼技侦那边能有新的线索,也希望那辆运毒车能够经过自己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