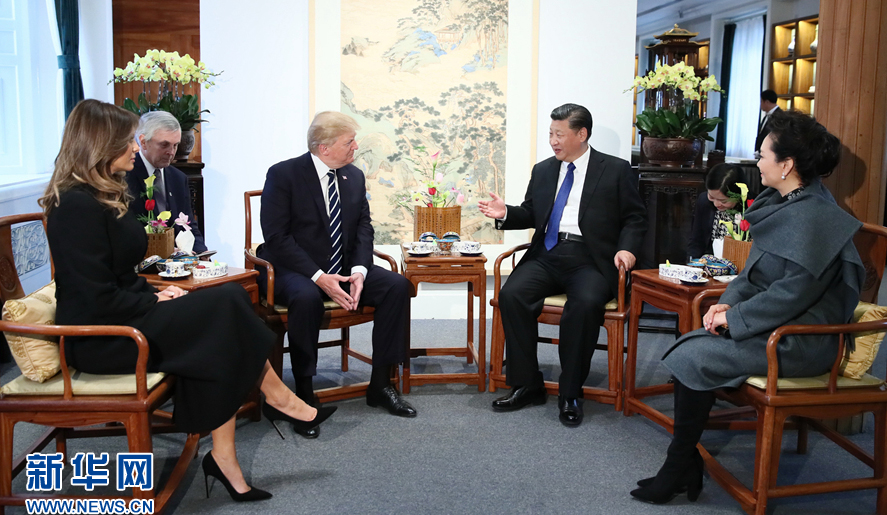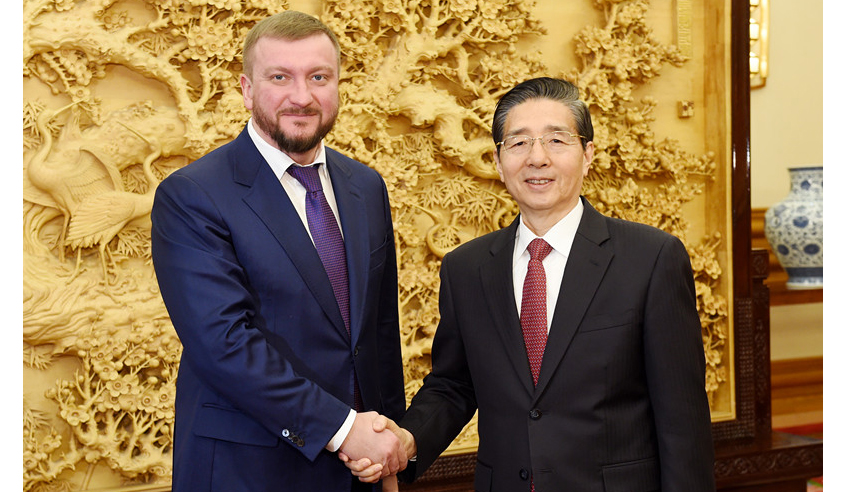一夜朔风,寒气南侵。穿着单薄的衣衫,钻进肆虐的寒风里,不由得缩紧身子。与初冬的照面,从一场寒风开始。
立冬过后,白昼渐短,黑夜渐长,昼夜温差大。由于寒暖空气往来冲突,有时会出现雾霭现象。雾散日出,河谷熠熠生辉,天地和暖人舒畅,小阳春原是如此之妙。曾经令人生畏的烈日,此刻却温顺得如一只羔羊,正午的阳光特别让人依恋。
田垄间,红薯,豆黍,苞谷,稻子,棉花,刨的刨,割的割,拔的拔,最终悉数归入仓廪。有了谷物打底,主妇不再显得局促,而是使出浑身的解数,不断翻出新花样,小日子从此有了生气。将捶下来的谷物磨成粉,抟成一颗颗丸子,丢进翻滚的米汤里。稍等一会儿,黏黏的粥便成了。红薯贴上锅沿,蒸熟后结了一层茧子,每每在饭前吃几片沾着饭糁子的红薯,先垫垫肚子。讲究的人家将红薯切成片,晒干后可以生吃,也可以与稀饭搭在一起吃。
这个时节,园子里像样的蔬菜屈指可数。不过,经霜后的白菜绝对是蔬菜中的上品。洗净,切碎,放在油锅里清炒,色泽鲜嫩油润,吃起来甜滋滋的,如果再来一碟水磨的辣椒,那会让你胃口大开。白胖胖的萝卜也成了新宠,可以腌制,可以制作萝卜干,冬天里哪家不储藏几坛。选个晴朗的日子,洗净坛坛罐罐,将土里土气的萝卜一股脑儿倒进木桶或木盆里,再一个个地刷洗干净,或切块或整个塞进坛坛罐罐,撒上盐,封好口。过些日子打开,拣一个萝卜头,咬一口,嘎嘣脆。若是做萝卜干的话,就要切成长条形,散在草席上晒一晒,直至变成“僵虫子”,然后在沸水里焯一下,晾干后拌上调料,便成了五香萝卜干,又香又脆,整个漫长的冬季都可享用。
接下来,就要弹几床棉被准备过冬了。收拾好棉花,请来棉匠。将棉花摊在木板上,棉匠一手执大弓,一手持木榔头,不停地敲击弓弦,发出“嘣嘣”的响声。经过一番敲打,一堆乱糟糟的棉花竟魔术般地变成一床蓬松的棉被。“檀木榔头,杉木梢;金鸡叫,雪花飘。”弹棉花是个细活。一床棉被弹好后,要密密麻麻地网上纱线,然后压平整。用线也有些讲究,平常用的是白纱线,若是姑娘陪嫁的棉被,就要用上红绿相间的纱线了。
隔上三五日,再到原上走一走,你会惊奇地发现,脚下的土地每一次细微的变化,总能唤醒沉睡的记忆。当朔风呼啸而过时,苍黄的大地早已漂染成一片淡墨色,散落其间的星星点点的新绿,即使显得弱不禁风,却依然能点燃一片生机和希望。
与冷寂的原野相比,村庄依然是热闹的。某家来了客人,请左邻右舍陪客,一片喧闹之声。有时,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会提议,今年又是好收成,打算请剧团来唱几本戏,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演出那几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唱哪些戏也是事先定好的,最受欢迎的还是《秦香莲》《女驸马》。
立冬后,沟塘进入枯水期,大片的河床裸露出来,来不及退走的田螺、河蚬、河蚌便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人们架起一台台水泵,日夜抽水。沟塘快见底的时候,众多的鱼儿再也沉不住气了,啪啪地活蹦乱跳,捉上来的鱼儿分给每户人家。不久,干涸的沟塘涌来大批的挑夫,他们遍布在逶迤的河埂上,拉开了冬修水利的序幕,远远望去,十分壮观。
天水清相入,秋冬气始交。立冬是秋冬季之交,称为“交子之时”,故有立冬吃饺子的习俗。手捧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多少悠悠往事漫上心头。
( 季宏林 作者单位:安徽省无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