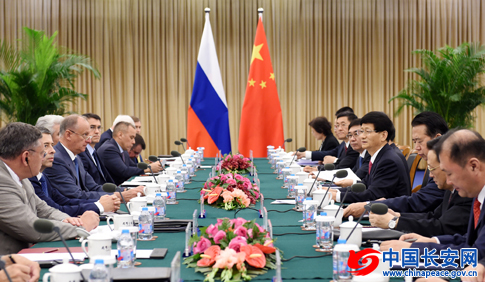曾经有一位评论家在文章中把我的作品归类于“底层写作”,这使我困惑了一段时间。并不是因为不屑于接受这样的名号,更不是对所谓底层有什么歧视,而是对“底层写作”这个提法,有些疑惑。
所谓“底层写作”,我将其理解为:指描写社会底层生活,或由社会底层人士撰写的文学作品或从事的文学写作活动。如前段时间爆红网络的打工嫂范雨素,因一篇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引发广泛关注和评论,算是所谓“底层写作”的一个范例。而我对“底层写作”的疑问,也由对此事的思考而渐渐明晰。
范雨素的写作,皮村的文学活动,还有打工诗歌的流传和残疾诗人的走红,都有着值得人们称赞之处。那种在逆境中的努力,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文学的热爱,值得每一个人敬佩。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顽固存在着的某种不平等意识,以及那一丝中产阶级的优越感,在上述对这些事件的报道中是被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这种加强或削弱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所为?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漫长进程中,文化的创造发展始终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状态。此消彼长,此长彼消,诸多文明成果在其中出现了反反复复的演变过程。如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本意是说君臣父子都要有符合自己身份的样子。但后来却在历史的推进中渐渐演变成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理论依据,成为儒家用以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教条。这样的教条,这样的精神束缚,不能不说至今仍然是社会中的顽疾,有着相当的市场,也是在关于所谓“底层写作”的讨论中,某些人所执的居高临下态度的精神内涵。
现实中,很有一些人是沉醉于自己的所谓阶层地位的。前不久从网络上看到一则消息,当然我希望是假的。说是某市某小区居民贴出了一则告示,对“低阶层人士”和他们共享这个高档小区的各种资源不满。这些“社会精英”的言行,其实很令有良知的人们所不齿。
因此,我不敢苟同“底层写作”的说法,我愿意把那些所谓“底层写作”称之为劳动者的创作。这样的创作其实有着更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有着更加丰沛的情感和带着泥土芬芳的质朴。这样的写作,恰恰是完全出自内心,少有金钱和功利的成分在其中。文字也许还不成熟,但精神高度是远胜于某些所谓精品的。
近日偶然打开电视机,正看到一部热播剧的片断。小流氓上门逼债,房主战战兢兢地捧出几个豆沙包,说兄弟你们先尝尝吧。流氓们吃了说好,问是什么牌子,答曰:思念。又问哪里有卖,说超市就有。如此的无聊,如此的荒唐,如此拙劣的广告植入,那些自以为高明的艺术家,你们在所谓“底层写作”面前,难道还会有优越感吗?
社会平等是社会学范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要警惕在我们当下的文艺创作中仍然时时有所流露的文化渣滓,要真正地关注和支持普通人在追求自己梦想中所付出的努力。中国梦不是一个虚幻的梦境,它是亿万中国人的小梦想融汇而成的伟大复兴之梦,是对建立富强、平等、公正社会的一种信念。
(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