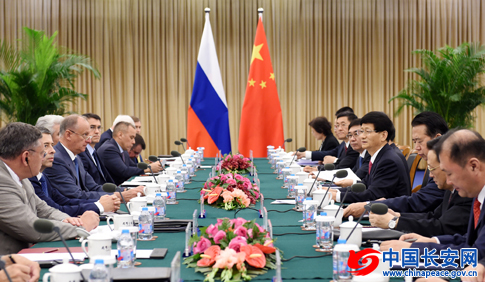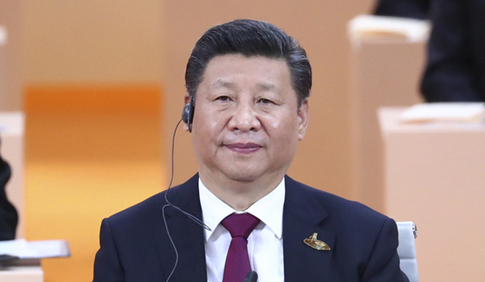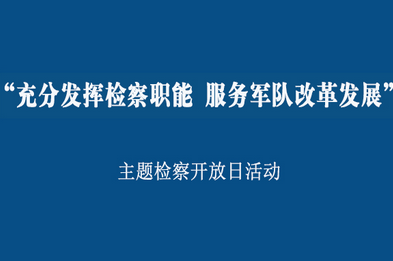在北方,面条代表了一份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说起面条,我对母亲做的手擀面情有独钟。记忆中,面条的制作过程是颇费一番工夫的。首先是和面,几碗干面粉,舀上半勺水,均匀搅动,少顷,待盆光,面光,手光,圆圆的面团就成型了,随后用擀面杖将面团压成扁平,转圈用力推碾,等厚薄均匀,母亲会把擀好的面一层一层折叠在案板上,每叠一层不忘均匀地撒上干面粉,以防相黏。然后切成宽窄适中的长条,用手抓散放到面板上,等水烧开下锅,片刻,煮熟的面条就上桌了。
手擀面的卤,最难忘的当然也是母亲做的。小时候,北方没有像现在这样四季有蔬菜供应,所以每年新鲜蔬菜上市的时候,母亲会把豆角和削下来的茄子皮用铁丝穿好,一串串晾在院子里,晾晒好后收藏起来,等用的时候泡发一下,切碎,用葱花配上辣椒一炒,美味无比。我最爱吃的当属芝麻酱面,但调制芝麻酱却不容易,太稀薄,味道会太淡,没有芝麻的香味,太浓稠,又不好拌开,口味也不爽滑。在我的记忆里,母亲调的芝麻酱总是恰到好处,舀一勺放面里,再撒上一点黄瓜丝,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母亲牌”面条就大功告成了。挑一筷子入口,满嘴尽是芝麻酱的香味与面的爽利,令人好不畅快。
小时候,喜欢吃的还有一种面食就是饸饹面。饸饹面是白面配着荞麦面做的,有时也会用上红薯面。压饸饹要用饸饹床,小时候,只有村东王大爷家有饸烙床。一根一米多长半尺见方的木头,在方木偏上的位置挖一个方槽,方槽的下方钉一个铁片,铁片上凿了好多筷子头粗细的圆孔,方木上头拴一根木杠子,利用杠杆原理将和好的面团从漏眼里压出去,一根根粗细均匀的面条便直接落在了滚沸的水里。只需两个翻滚,然后用漏勺将面捞出放入碗中,再往饸饹面里浇上熬好的清汤,几片瘦猪肉,浇一勺明油,洒上一撮香菜,美味无比。在那以后的好多年里,都是我记忆中粗粮制作的典范。
工作了,吃得最多的当属方便面了。这种面食吃起来方便简单,只需开水一壶,有时会加根香肠或加个卤蛋,无论是半夜巡逻人困马乏时,还是和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通宵熬夜时,来桶方便面,总会让人精神振奋,短暂缓解身心的疲惫。然而方便面吃多容易反胃。犹记得曾经连续几天通宵熬夜办理案件,工作间隙总少不了泡面相伴,以至于在案件审理完毕后,几个参战的兄弟每每提起“方便面”三个字都会反胃。但下次加班加点的时候照样还是少不了方便面的陪伴。
这些年来,品尝过不少各具特色的面条,陕西的油泼面,山西的刀削面,河南的烩面等等,可谓花样繁多、“面面俱到”。奇怪的是,却总吃不出小时候那种醇香的滋味和感觉,也许东西味道变了,也许是生活的环境变了,总之,那份美好只能在记忆里回味了。
(郭军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