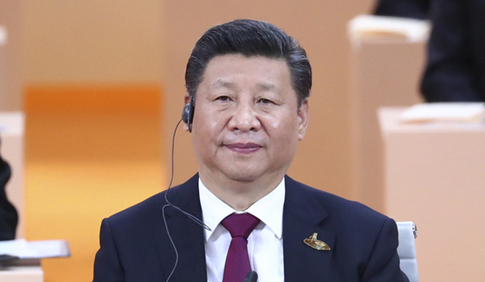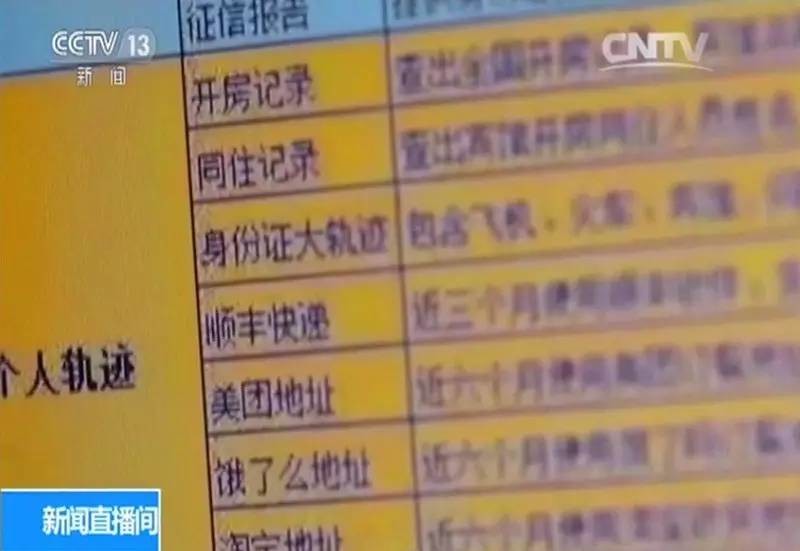下午给复旦的高中生夏令营开讲座,《镜头里的消失与发现——文明变迁中的中国人》。两个半小时,大家都很高兴,从一幅幅摄影图片中体会时代交替。
看着台下青春的面容,都那么认真,神色里都有对未来的向往,心里很感动。感动之下,还有些遗憾。这样的讲座是一次性的,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要进入复旦,但以后不可能整整齐齐再看到他们了。他们听得很仔细,也许会深深地记住。但我最大的希望,是能够讲一学期,让他们听着听着,萌生了独立思考,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最后都不同意老师的见解,走上深入思考的小径。这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是一个老师最大的幸福。
本科时读过几本哲学史,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哲学家都是在批判继承前一代的基础上不断前行的。十八世纪中期休谟和洛克的经验主义广为传播,《人类理解研究》被奉为圣典。晚生的康德以《纯粹理性批判》揭示理念对经验的统调作用,将真理性赋予超验的“纯粹理性”。后来的黑格尔看到康德哲学中仍有不可知论的缝隙,写下《精神现象学》这一大作,奠定“自然可知论”的基石。其后,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哲学家,批判继承黑格尔者络绎不绝,形成了哲学发展的又一番风景。
被学生批判是不容易的,首先你要值得被批判。成为一个有价值的批判对象,这是一个教师一生的追求。在这种批判的关系中,包含着文化最深的尊重和承继,也渗透着最真挚的感情。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面对他的老师柏拉图,他的“吾爱”是发自内心的敬重,而“更爱”是师生对于真理共同的敬仰。
今天刚刚在亚马逊订了一本《世界哲学史》,德国人汉斯·施杜里希写的,600多页,不可能一气读完,只能挑着看。春天就看到这本书,犹豫着没有买,因为手里有好几本厚厚的哲学史。昨天看到同为著名哲学史家的美国人古斯塔夫·缪勒推介说:“对于初次接触哲学、想要有个好开头的人来说,本书是绝佳的读本。”这话特别符合我自己的定位,赶紧买一本。收到以后,首先要看的肯定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的思想波澜,那古远的真理之光,是多么单纯。
(梁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