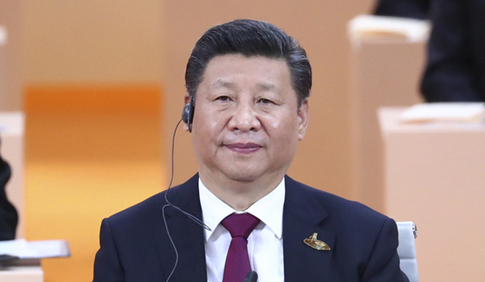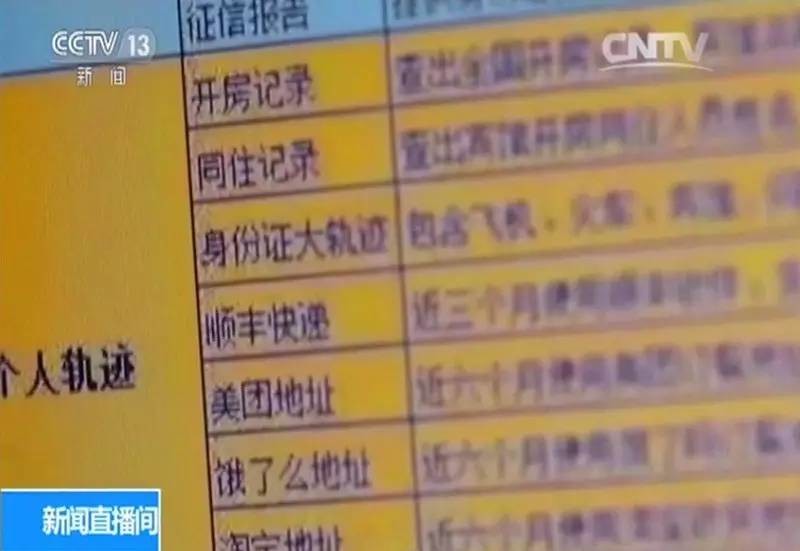她的故乡、她的南岸,因她而美,而永存——□木 汀
每当在烈日或雨中的街头闾巷见到他们熟悉的身影,总会想到这份职业的不易;每当看到他们威武英勇地震慑邪恶终结罪恶,总会想到、感受到我们的平安来自他们时时面临的险境……他们是人民的卫士——公安民警。
我一直对人民警察充满敬意,他们是社会稳定、民众安居的基石。社会治安、交通畅行……即便是小到家长里短的纠纷,只要他们在,心中那份踏实油然而生。我无法想象如果世间没有了他们,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混乱无序或危情四起。
我对职业为公安的诗人更充满敬意,他们在履行职业所赋予的神圣职责之外,在面对着太平盛世的表象下,那些隐藏着的险恶和丑陋的同时,还能在心中拓出或是坚守着那一片清淳宁静的家园,以此追随着灵魂的诗意。
前些日子在广西南宁,我向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杨锦求证,全国公安民警中,业余从事诗歌写作的有3000人吗?
杨锦给我的回答超出我的意料:远远不止。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我完全确信这个数字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我记得全国公安文联副主席张策在为《琴剑诗系——全国公安实力派诗人丛书》作序时,曾这样写道:不能想象警察没有诗歌。用枪写诗,血与火是我们青春的色彩;用泪写诗,生与死是我们忠诚的宿命。在追捕在逃凶徒的千里征途上,风花雪月都有了别样的寓意;在维护安宁的岗位坚守中,春夏秋冬都有了别样的风景。诗歌,是最能抒发警察心境的语汇,是最能表达警察品格的叙事。诗歌,已成为中国警察灵魂里的一支血脉,它流淌着勃勃生机,孕育着我们的另一颗心脏。
如今,公安诗人苏雨景的诗集在我的书架上,常常在我安静时,被抽出来反反复复阅读。我之所以说在安静时阅读,是因为阅读苏雨景的诗,需要一种仪式,而安静是最好的阅读仪式。当我翻开苏雨景的诗集,就一步步地踱进了于我虚拟而于她真实的那个世界。她的诗是可视的,可听的,可闻的。
比如《偶然》:
……
偶然 我在相册里见到了父亲
伸出手 想用食指和拇指除掉他的白发
可满头风霜
我该除哪一根呢
……
这淡淡的几笔,便能戳中读者内心的酸楚,似乎闻到了庄稼收割后翻起的属于田间土地的味道,疲惫却隐藏着生机的味道。想必苏雨景笔下的父亲,她相册里的父亲,与无数人的父亲一样,都是那样的沉默、木讷、坚忍,而又与世无争无求的吧?
比如《“特5”路上》:
从南站到白云路
她一直大着嗓门说话
她说到稻谷 说到玉米
……
说到年久失修的宅院
说到乡邻中的一些人 说到思念
……
我好像也听到了在熙攘的烦躁的路上,在一辆发动机轰鸣、人声嘈杂的公共汽车里,一个外地女人举着电话正在和老家的人闲扯。而令我愧颜的是,也许我会侧目而怨的那种嘈杂,于苏雨景耳中,却让她看到了“她把手机从左手换至右手 继续紧紧地握着/握着一只远方伸过来的大手”。我想,诗歌对苏雨景而言,是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的,这种力量让她内心充盈着美,继而才会看到,才会听到繁芜世间的一丝美好吧。
苏雨景的诗歌写作的视野较为宽泛。除了书写故土和至亲、生灵和四季的景致,还有她的职责、战友。她的组诗《从警的N种况味》,每一首都只有三行,就是这短短的平实的三行诗句,也饱含着她对公安职业的忠诚和无怨无悔:在案件久侦不破的失眠夜,缠绕着她思绪的除了案子竟还有海子;在英雄山下执勤时擦肩而过的那么多冷漠的面孔,都是她的牵挂;她守着城市的夜也念着故乡的白发……警察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无可复制和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正如我在第五届“夏青杯”全国朗诵大赛中,应邀对公安赛区的参赛选手们点评时提到过的:“细节,是文本的独特性和艺术感染力最重要的构件”。组诗中的这些作品在细节捕捉上的巧妙和灵动,让读者不仅看到了警察工作的片段,更体味到了一位女警对待警察职业的那颗太阳般的心和对待家人、战友的月亮般的柔情。
苏雨景是鲁北人,尽管工作和生活始终是在齐鲁大地,且鲁北“近在咫尺”——即便如此,但于她内心,还是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故乡——这种“脆弱”,发轫于她对那方土地的念念不忘与不舍,她曾写道:“直到多年以后,我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骨血里的故乡情结才越来越强烈起来。每每回首,故乡就端坐在岁月的景深里,仪态安详,散发着母爱的光。”
对于所有的游子来说,故乡的神经遍布于眼、鼻、耳和内心,随时都可能被触动并牵肠挂肚。故乡是苏雨景的精神家园,诗变成了她这个家园的载体。苏雨景对故乡的钟情是那么的绘声绘色和记忆犹新。父亲和母亲之外,她记得那只卑微的羊,她记得时时想起都万般亲切的乳名,她记得那一株象征生命的麦子。
和故乡对话,和职业对话,和思念对话,和未知的世界对话,苏雨景自己说,故乡是诗歌的根,在我看来则不然。诗歌是苏雨景内心的雨。对父老乡亲的深深眷恋是她头顶上那片时明时暗的云朵,准确地说,故乡是她诗歌的大地。
如果说当下诗歌(指新诗)仍陷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那么,这是诗歌(指新诗)背离读者、背离人民这块土壤而作茧自缚所致。作为诗歌工作者,我坚持不懈地宣扬艾青的诗歌思想,即:朴素、单纯、集中、明快。我持续关注着这些职业为警察的诗歌写作者,是因为我认为他们的作品,最接近艾青的倡导。他们不受各种诗潮所绑架,只尊重诗歌的本质,奉行诗歌的本质。
艾青把朴素置于诗歌写作首要要素,而苏雨景善于用朴素扣人心弦,来完成属于她自己的诗歌文字和诗的关系。
我倏然想起她在一首诗中写到:“相濡以沫这么多年 早已彼此习惯/最爱我们在一起的样子 说/是世上 至美与至美的叠加……”我想,她与故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她的故乡、她的南岸,因她而美,而永存,而苏雨景,这位鲁北的女儿,她呼吸的是故乡的光,即便在冷峻的警服下,也散发出温暖的诗意和善良。(木汀,原名杨东彪,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