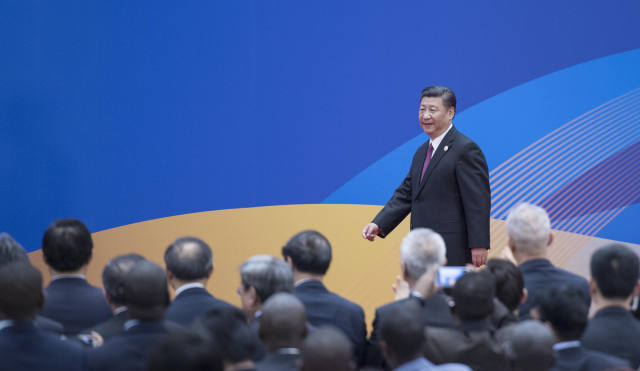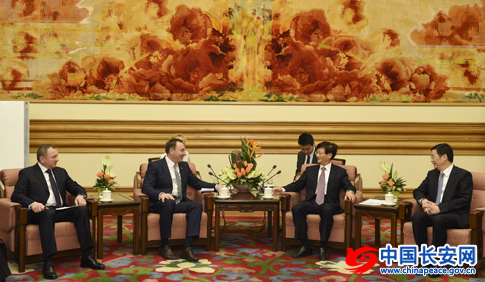扶栏的那一刻,突然又想画花鸟了。
那一天,我从8楼阳台上往下望去,园子里柳枝团团簇簇高低起伏,错落在小巧精致的亭台水榭间,在3月明亮的阳光下滋滋生长着,舒展着,充盈着一片绿意,撩得风里也都有了青翠的调子。不知什么鸟儿一声啁啾,婉转悠长,浸没在枝枝叶叶中,像是在诱惑着什么。我转身下楼来,园中小路曲折着,通向花木繁茂的深处。大概是季节正合适吧,茶花兀自开着,那株路边粉色的樱花树,不知什么时候撒开薄纱般的雾幔,把人们罩回小时候的梦里。
熟悉的人都知道,我是喜欢这等园林景致花草林木的。
当年学画,曾经问一位老师,画什么好?他说,当然画山水。我问为什么,他说山水画集天地山川万象,自然为创作之首选。不过女性习画多喜花鸟及工笔。可是,花鸟容易落俗。老师说完,我心中顿生几分对山水的向往。想着当年临摹《芥子园画传》,也应该算是有几分的童子功功底,一时间竟有点心神不定蠢蠢欲动了。
没几天,一位朋友发来一条彩信。打开,一幅烟雨苍茫瑰丽绚烂的巨幅山水画卷呈现在面前。天呢!我从心底里惊呼一声。气象万千。这才是气象万千哩!那一瞬间,我完全读懂了这个词的全部意义。知道谁的吗?朋友故作神秘。张大千的《庐山图》啊!这幅作品早就听说,那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于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开始了创作。
作画真是个神奇的事儿,一旦上手便欲罢不能。点线面,勾勒皴,再加上构图布局气韵,无论哪一方面都那么让我着迷,我真的一头扎了进去。范宽、郭熙、石涛,水墨、重彩、泼彩,那些日月星辰,那些山川花木,都让我如痴如醉。我去了太行山,领略它刀削般悬崖绝壁的沧桑伟岸,也见识了通天峡高山平湖深潭瀑布;又去了泰山,感叹它“一览众山小”的雄奇险幽;还去过庐山,望庐山瀑布千古长流,感叹襟江带湖的秀丽迷人;更是三上黄山,领教莲花峰、天都峰的鬼斧神工,陶醉于黄山云海的神秘莫测、出神入化之中。我尽情地欣赏着,解读着它们,我在不停地行走。
那个踏雪而归的冬日,我疲惫地回到家中,如释重负。人在旅途,终究是累的。半醒半睡之间,一缕香气似有似无地滑过,像雾,像雨,又像风。我从梦中醒来,端坐,磨墨,铺纸,运笔。
我的心里一片清宁,只有花开的声音,也有露珠的清凉,还有天鹅羽翼上的霞光。想起小时候后院那个大花园,四季次第开放着花儿,芍药、月季和金针,还有我们的嬉戏、笑闹。那个时候,风在跟着我们飞舞,阳光拥我们入怀,泥土被我们唤醒了芬芳。数年之后去了云南,迫不及待的我甩开同伴直奔香格里拉,扑向香气氤氲一望无际的花海草甸子,狠着劲儿打了几个滚。我这才知道,走过多少年,无论走过多少山川河流、层峦叠嶂,自己的心里,一直驻着那个百花园。
老师说,你的花鸟画,不俗。
有些日子了,池塘在温暖的春阳下波光粼粼,晶莹而又温润。靠岸的这边落红片片,是茶花瓣呢,却犹如妙手上的唇彩。
我知道,栀子花又要开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公安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