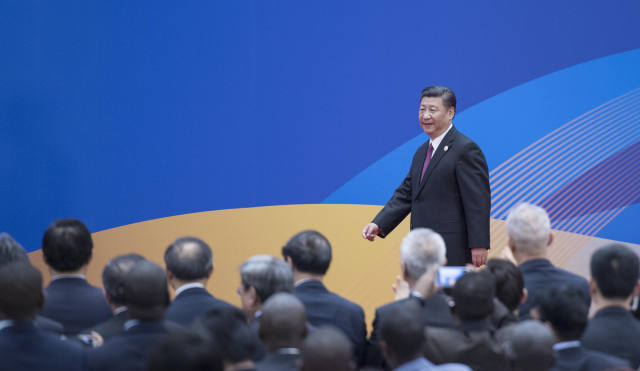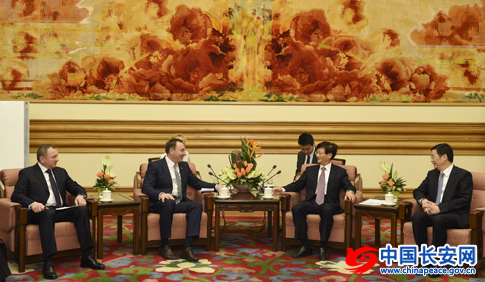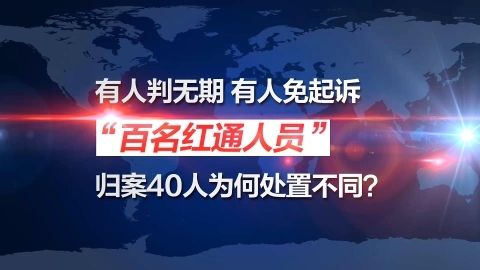在一般观念中,对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学说,人们多注意其尊崇儒术、张扬君权之功,而忽视其对世俗政权在政治观念上形成的“在先约束”。实际上,董仲舒法律思想中颇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天道观念,恰以其超验性价值为汉代以降的皇权体制设定了一道不难索解的“政治紧箍咒”。
秦汉之际,风云翻覆,古老的神权政治和源远流长的以血统为划分标准的贵族政制被打破,由布衣天子所建立的汉帝国初创之时便面临两个较为突出的政治问题——一是非贵族血统的平民政权如何证明其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问题;二是如何在大一统的帝制时代防止君权无限膨胀的问题。正如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汉朝新生的皇权官僚政治“没有贵族政治那样外部的一目了然的自然血统条件可以依据”,所以必须“托之于天,假手于不可见、不可知的冥冥主宰,以杜绝野心者的非法凯觑”。因此,若不能证明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则无法阻挡草莽英雄们滋生“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政权的更迭则不再遵循“受命于天”的权力继受逻辑,而会遭遇“成王败寇”的合法性危机;同时,在缺乏贵族政治约束的情况下,如不能妥善解决君权膨胀问题,则新生的政权很可能重蹈秦帝国败亡的覆辙。因此,既要“推崇君权”又要“约束君权”,这个看似悖论的政治难题至汉武帝时,终于由大儒董仲舒创制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予以解决。
按照董仲舒对政治法律秩序的设计,在世俗政权之上应当还有更高的超验价值存在,人间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权力秩序安排,必须符合“天道”。君主虽然掌握政治上的最高权力,但并无垄断道德判断的权力,君主只有顺应天道才能具有合法性,进而通过代表上天的“道统”来制约代表世俗君王的“治统”,而这种“道统高于政统”的传统儒家精神正是“从道不从君”观念的来源。
实际上,早在商周时代,统治者便以“受命于天”、“恭行天罚”的天道思想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西周政权为了解释何以能取代过去一直被认为代表神圣天命的殷商政权,主动降低姿态,提出“天命靡常,以德配天”,即上天并非永远眷顾某个家族或政权,神秘的天道与世俗政权之间以民心相背维系。国运兴衰紧紧依附在天道与民心之中,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的设定。这一微妙的转变,使得天道思想作为超验正义观念一方面为政治提供了最终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世俗政治必须接受天道的约束而不能肆意妄为。
因此,“天人感应说”一方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渊源,一方面则假天之威,提出了对皇帝言行的要求。在这里,董仲舒修正了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转而以“天贵君轻”的方式使君权的神圣性降格,让自命不凡的君主心有敬畏。也就是说,“天人感应说”在为一个平民化的皇权官僚体制建构“合法性”的同时,也意在实现对于君权的适当限制,这正是董仲舒苦心孤诣推演出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在此语境下,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意志来行事,并通过布施仁政而获得长治久安。至于何为天命、天道与仁政,具体解释权则掌握在儒家知识分子手中。甚至可以说,在今天看来似乎与司法专业化背道而驰的“春秋决狱”, 在当时却意味着以春秋经义中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的自然法则超越皇帝的制定法,以具体判例中的伦理精神来平衡严苛的律条,并演化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法律渊源。
至此,儒家知识分子足以运用儒家伦理传统、个人德行与专门知识来抗衡强大的皇权力量。这样,超验价值就对世俗政权形成一种持久的约束,任何无视和否定超验价值、任凭君王个人意志决断一切的行为都将被宣布背离天道。唯其如此,对于始终追随并捍卫这种价值的儒生们来说,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精神和牺牲精神才真正产生意义,而这也正是董仲舒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所延展出的超验正义之所在。
(张文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