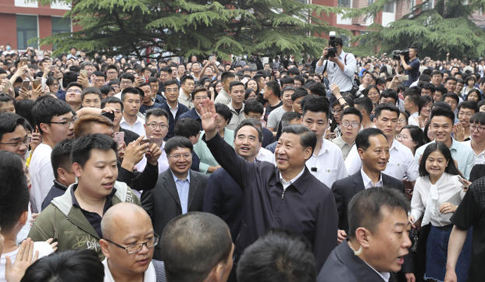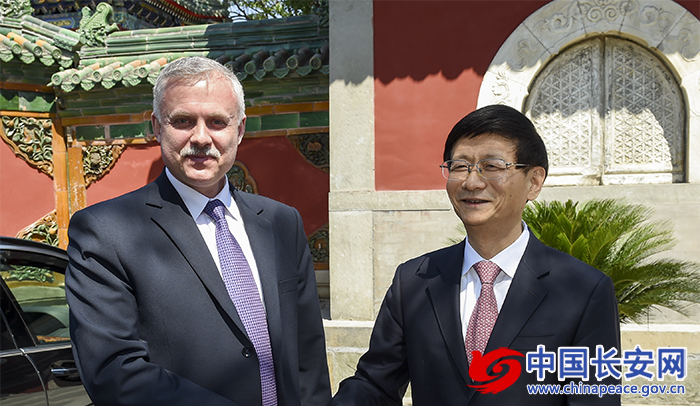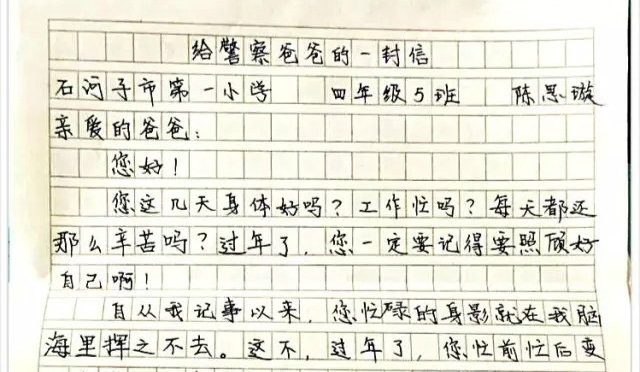“欧文龙系列案”被澳门喻为“世纪巨贪案”。欧文龙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前运输工务司司长,是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以来因贪腐下台的最高级官员。2006年12月因涉嫌巨额贪污案被廉政公署拘捕,2009年4月,经澳门终审法院裁定,滥用职权、受贿、洗钱、财产申报的虚假声明及财产来源不明等81项罪名成立,判处监禁28年半。该系列案件中的其他嫌犯也被判处清洗黑钱罪和行贿不法行为罪罪名成立。无论从情节严重性还是身份特殊性,该案件都得到公众关注并引起社会热议。澳门特区各级司法机关在办理欧文龙案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国家“尊严”和“声誉”的法益保护和法治追求,对我们当前进行的反腐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于受贿罪的一般法律制度,《澳门刑法典》第五章(执行公共职务时所犯之罪)第二节(贿赂)中的第337条和第338条对此进行了规定。通常而言,第337条的规定情况要求公务员的交换条件是违反职务上的义务,是真正意义上的受贿;而第338条的规定情况要求公务员的交换条件不违反职务上之义务的作为或不作为,是非真正意义上的受贿。也就是说,如所作出的作为或不作为违反其职务上的义务,则属受贿作不法行为。如所作出的作为或不作为不违反其职务上的义务,则为受贿作合规范行为。法官在判决中引用A.M.ALMEIDA COSTA的解释,受贿罪背后所要保护的法益为国家的“尊严”和“声誉”,体现于集体对国家机关运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的“信任”,是受贿罪固有的法益。保护的目标就是国家的声誉与尊严,而这些是赋予国家追求合法利益过程中具效率或开展工作的前提要件。
在此案中,欧文龙触犯了受贿作不法行为和受贿作合规范之行为两个罪名。按照起诉批示第623条中使用的条文编号(从1到41),第1、2、6、22、23、26及27项中,欧文龙命令在执行公共工程承包公开招标时,令其下属改变其自由和技术的选择,向他提出被告想中标的公司的行为违反了规范所提到的公开招标的多项原则和法规;在第29、30、37及39项中,欧文龙为获取金钱利益而作将公共工程或服务直接批给相关企业的决定并非根据公共利益标准去作出选择,而是他的个人利益;在第3、5、7、10、24及25项中,欧文龙公然违反规范选择的规则,不顾评标委员会或负责对标书作技术评定的机关的技术观点为何,口头指示建议有关部门将一项公共工程或服务直接予以特定的公司。另外,在第13项中,欧文龙强烈地参与其中,收取了3200万澳门元,并虚假地通知土地工务运输局有关将来交通网络的地点,以便有关项目获批准。在第40项中,欧文龙在某许可的申请没有任何新事实情况下命令土地运输局重新审议请求,最后同一工程师和土地工务运输局都变更了之前的决定,判决中法官认为这是改变技术员的意见书和土地工务运输局局长决定的“邀请”。在第41项中,欧文龙向利害关系人提出支付一个商铺作为批给土地的回报。以上这些行政行为明显违反了职务上的义务,均符合《澳门刑法典》规定的第337条的犯罪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欧文龙在进行答辩的过程中提到:政府司长不受“勤谨、无私和公正义务”的约束,认为不应该排除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司长们在他们具有直接或间接个人利益事务上作出干预。这是相当荒谬的观点。因为根据《基本法》第61、62和64条的规定,以上所述的这些人在执行公务时必须遵守法律。根据《行政程序法典》第3条和第4条规定,公共行政当局机关之活动应遵从法律且在该机关获赋予之权力范围内进行,同时其有权限在尊重居民之权利及受法律保护之利益下,谋求公共利益。该法第7条题为“公正原则及无私原则”,明确规定:“公共行政当局从事活动时,应以公正及无私方式,对待所有与其产生关系者。”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在判词中用“独特看法”来形容欧文龙的这一口头陈述。这一观点实际上与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混淆。这种自由裁量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只为其自由裁量权的法规所要求的公共利益而作出的。所谓公共利益,可以从公共工程的报价和质量的方面考虑,可以对照澳门民用建筑的实际情况,可以参照国际上各国家各地区的一般安全标准等等。如果行政当局在作选择时所考虑的决定性原因并非该权力所要追求之目标,那么该权力的行使必然出现“权力偏差”的瑕疵问题,公众的利益必定受到侵害。因此,这种权利应当是有限制的有约束的。
根据F.L.COSTA PINTO的观点,对所有行贿受贿行为予以刑事归责所要保护的法益为“行政合法性”是一项宪法性价值和法治国家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任何市民与国家交往中的一种辅助性利益。欧文龙的行为极大地破坏了澳门特区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损害了法治制度,充分显示其公然敛财,践踏法律,犯罪情节极其恶劣,对社会的影响极大,因此必须以刑事归责方式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制裁,这体现的是宪法性的价值,是法治国家的要求,也是国家与国民利益互相交换的一种良性模式。
(卢颂馨 作者系澳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