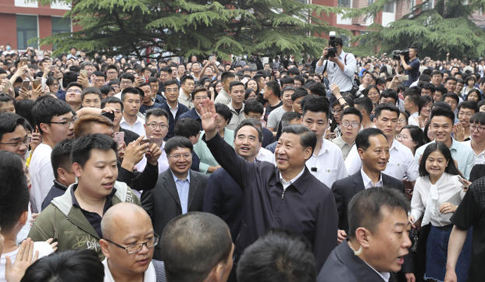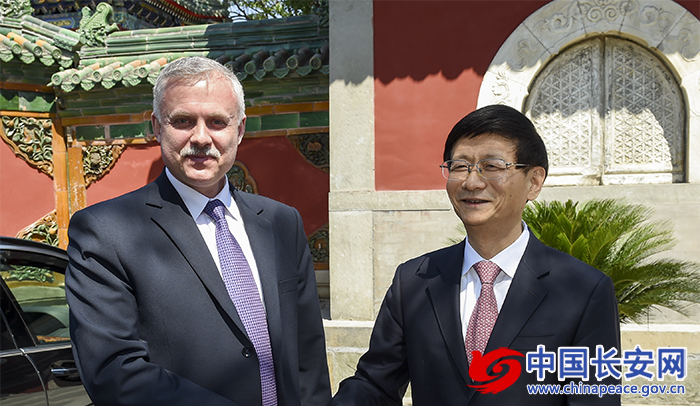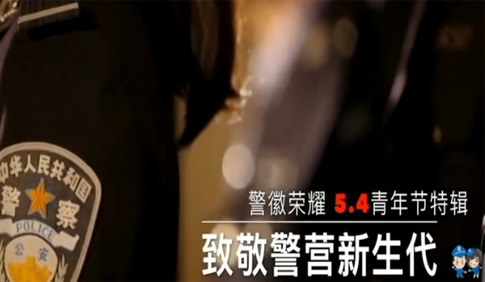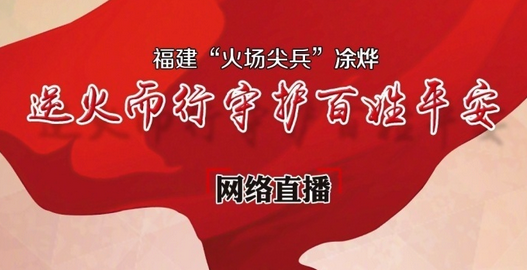出于对大跨度时代变迁题材小说的偏爱,一口气读完了格非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之作——《江南》三部曲。掩卷回味,那种精神上的迷茫与沉痛,对时代隐晦地探求与追问,在内心强烈共鸣。
《江南》三部曲时间横跨百年,以江南城乡为缩影,以有血缘传承的三代人为主线,聚焦清朝末年民国初年、1952年至1962年间和当代中国三段社会巨变下,不同阶层、不同性格人物的人生际遇与精神求索。从《人面桃花》到《山河入梦》,再到《春尽江南》,绝美的书名里,隐喻着虚幻的浮华和缥缈的梦境,就像书中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注定要走向宿命的悲剧。
作为三部书主人公的母子、父子三代人,虽然血脉相接,但彼此间从未相识,更不相知;三段故事之间,也没有更多的承接关系。作者有意无意间,安排的这种记忆与历史的断裂,引人沉思。
与时代裂层相对的,是三代人精神特质的传承与延续。《人面桃花》里生长在官宦之家的秀米,《山河入梦》里秀米的儿子、县长谭功达,《春尽江南》里谭功达的儿子、落魄诗人谭端午,都有着对命运敏锐的感知与伤怀、对理想诗意的追求与忧郁。只是,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精神传承已日渐迷失和消亡。秀米“大同世界”的革命理想,混杂着她的爱情迷恋,坚定而执拗,从不受制于周边的环境与指摘。谭功达追求的“桃花源”式的理想图景,虽然内心里始终执著坚守,但受困于社会现实,言行上不得不屡屡退让妥协。到了谭端午,他的诗人理想早已全面投诚于时代喧嚣,他所有的懦弱、懒散、不忠、懈怠,归根结底,都是精神受挫后对一切都已无所谓的极度消极。正如一部小说中所写的,“活着就那么回事,既没有特别值得也没有什么不值得的。那是一种隔阂,跟生活,跟所有的人,也跟我自己。”而这,大概也是现今许多人真实的精神写照。
这种迷失与消亡,不仅仅停留在精神上。贯穿全书的“乌托邦”象征“花家舍”,从曾经户户连通风雨长廊、“蜜蜂都会迷路”的恬静小岛,物化为纸醉金迷的销金窟,昭示着理想的碰壁与沉沦。就连诗意的语言、美丽的江南都在日渐蜕变消亡,《人面桃花》里,春日的杏花烟雨、炎夏的荷花满缸、秋季的红果薄霜、冬夜的腊梅冰花,都如诗如画、优雅从容;《山河入梦》中,宿命的苦楝树、缤纷的紫云英、红艳的桃树林,绚烂夺目,让苦难也多了一种悲情的美感;而到了《春尽江南》,已“几乎看不到一个村庄”,引得文艺女青年慨叹追访的“渔火”,不过是垃圾填埋场的夜灯。一切,都污秽而颓废,错乱而荒谬。
三本书里,格非分别用灯灰冬雪夜长、海水围困的孤岛、祭台上的月亮,营造了三个清寒孤绝的冰美意象,预示了三位女主角不可逆转的孤寂死亡,理想主义的挽歌在全篇回响。人的面目越来越晦暗,岚早成霾,哪有什么乌托邦,什么诗与远方……
好在,《春尽江南》的最后结尾,谭端午在妻子死后,将自己那首没有写完的诗改名后续写发表,从虚无冷漠的“祭台上的月亮”,到现实中可以触摸呵护的“睡莲”,谭端午在自我审视中重拾过往,渴望着精神的回归和现实的变革,也寓意了未来与希望。
就如每个人心中都曾有过的那点理想微光,哪怕在现实冲击下,弱如冬夜残灯,远如海中孤岛,淡如清冷月光,依旧需要坚守与呵护,就算永远也无法抵达,依然会在内心指引闪亮,即便徘徊迷茫,终将免于沉沦,免于消亡。
是为初心。
(郭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