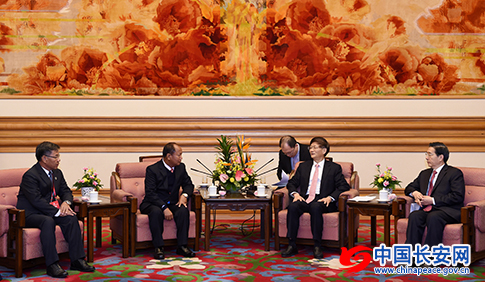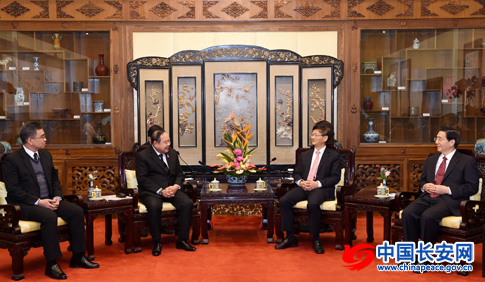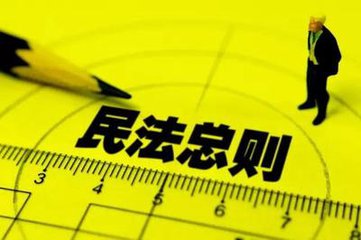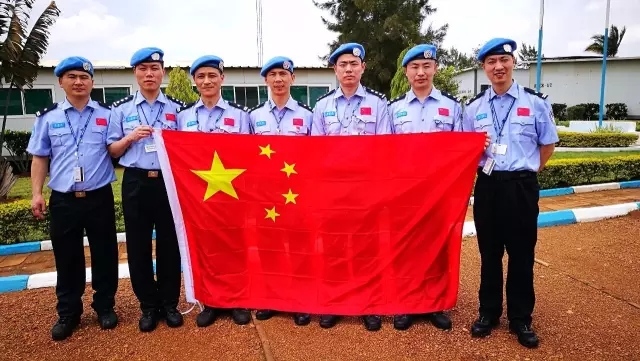观影《十二公民》:
“疑罪从无”乃法治精神的应有之义
“疑罪从无”乃是有利于被告原则在刑事法律中的贯彻已成为各国刑事司法领域的重要共识。不论是从逻辑理论上还是实践理性上来看,“疑罪从无”都是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重要规则,其在保障人权、防范错案冤案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徐昂执导的《十二公民》改编自1957年的美国影片《十二怒汉》,全篇讲述的是十二个职业背景、知识背景各不相同的公民对一起“富二代杀父案”进行审判的故事。看完此片,我触动颇深,因为片中所体现出的在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必须要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精神正与当下法治建设不谋而合。
一个随母改嫁的孩子成为了人们眼中的富二代,其生父一直从他那里勒索钱款来吃喝嫖赌。一天夜里小伙子探望生父后,其生父被谋杀,案发现场遗留一把富二代车里常备的侧跳匕首刀,被认定为物证。据其生父楼下腿脚不便的老人证实,听见楼上父子争吵时儿子说:“我要杀了你!” 十五秒后老人看到富二代跑下楼梯,而其生父已死。与此同时,离建筑物不远处的火车上一青年女子透过车窗看见了富二代行凶杀人的全过程。
富二代与生父不合、矛盾不断,其具有行凶的动机。从证据上来看,犯罪现场遗留的匕首正好富二代也有一把,并且恰好丢失;楼下的老人证实其听见富二代说“我要杀了你”,并有火车上的一名女青年看见了富二代行凶的全过程;所有的人证和物证都指向了富二代弑父,新闻媒体也都毫无例外地认为富二代行凶。所以,富二代有罪还是无罪似乎不是问题。在十二个公民组成的小陪审团进行的第一轮投票以11比1的绝对多数认为罪名成立,而法学院模拟法庭的要求必须是12:0通过。所以,有罪还是无罪在陪审团成员间展开了讨论。

在这十二个公民当中只有8号陪审员认为富二代是无罪的,当然他并没有证据证明凶手另有他人,他主张应以更加审慎的态度来审视这个案件,因为他们的审判涉及到一个孩子的生死,谨慎、认真、负责任的行使手中的权利自不待言。在激烈的讨论中,那些原本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证据的真实性出现了疑问,也就说认定富二代有罪的证据存在着诸多合理怀疑。
第一个怀疑便是遗留在现场的匕首,那是一把很普通的匕首,随便花几十块钱在网上就能买到,而又没有指纹鉴定说现场遗留的匕首上留有富二代的指纹,所以不能排除其他人用相同的匕首杀害其生父的可能性;
第二个怀疑便是楼下老人的证言,经过现场测验一个腿脚有残疾的人无法在15秒内完成他所说的从床上起来然后出去打开门看到富二代刚好下来,而且在火车经过时巨大的噪音下他也是无法清除听见富二代喊“我要杀了你”的;
第三个怀疑便是声称看见富二代行凶全过程的女子在睡觉时还戴着眼镜是违背常识的,如果不带眼镜她又无法清楚地看见行凶的过程。正是这些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促使一开始主张有罪的陪审员走向了另一个阵营。

从开始的11:1主张富二代孩子有罪,到最后发生惊天逆转,最终以12:0通过了他无罪。其他十一个公民从主张有罪的阵营走向对立方,并不是8号陪审员提出了证据证明富二代没有杀人,正如他所说的找出证据证明富二代有罪是警察的职责,作为审判陪审员的职责就是基于现有的证据能否作出有罪的判决。结果是不能作出有罪的判决,因为他们无法排除8号陪审员所提出的诸多合理怀疑,尽管凶手很可能是富二代,但就现有证据而言无法作出百分百的论断,就应该判决他无罪,这应当是法治精神的应有之义。
在认定犯罪嫌疑人罪名成立时主张排除合理怀疑正是疑罪从无的思想内核。虽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的法治原则,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形却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个中缘由颇为复杂。所以,即使是在法治建设已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的当下,我们仍有必要对疑罪从无进行研究和呼唤,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十二公民》所带来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影片本身,而化身为法治的“传声筒”。(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