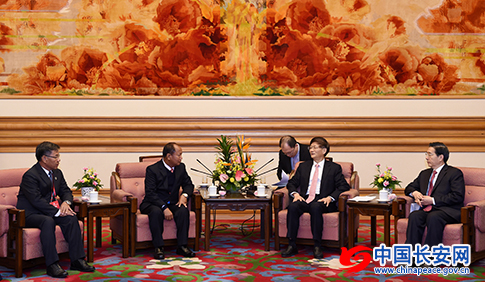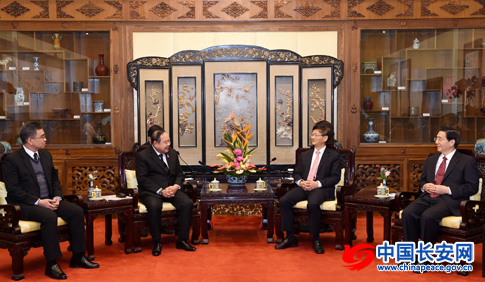当我在寒冬,辗转回到长白山深处、鸭绿江畔的小山村,记忆中的很多人已经作古,或者如我,离开清冷的山村,去了广阔的天地。儿时的玩伴几乎寻不见了。嫁进山村的女人,和她们养育的孩子,我全然不识。曾经近在咫尺的邻居,我应该称她婶婶,她站在车辆奇少的岔道口,依稀可见年轻时的模样,惊奇地望着我问:你是谁家的亲戚?
我不禁自问,我远离过故乡吗?
我仿佛看到,山下鸭绿江上的积雪,正在耀眼的春光下悄悄融化,坚实的冰面日渐酥软,分解成大小、形状不一的冰块。某天清晨,游移在江面上的冰块,突然一下全部消失了,大江豁然壮阔起来。山村陡然显现出了勃勃生机。等婀娜的江柳,被柔软细腻的风吹拂出毛茸茸的白花,江鱼的鳞片更加白亮,铁锅炖江鱼的鲜美滋味于是成为了舌尖上的珍藏。
还有陷入连绵细雨中的村庄。江水在一片烟白中暴涨,潜进村庄,小心地拍打着大门前的石阶。情势貌似紧迫,却没人为此担心。江水再汹涌,再波澜壮阔,又能高出下游水电站大坝几许呢?
浩浩荡荡的江水,犹犹豫豫地消隐下去。第二年很可能是旱年。饱含雨水的云朵,不知都飘去了哪里,没有雨水注入,原本千帆竞过的宽阔江面,日渐枯萎,烈日下渐渐消瘦到叫人揪心。早先沉在一江碧水里的旧村遗留物,比如残垣断墙、曾经的万亩良田,在几乎断流的袒露河床上,一览无余地重见了天日。田里的庄稼可怜巴巴,长辈们忧心忡忡,开始在灯下怀念旧村里的事物。
旧村岁月于我,是新鲜的,而并非沧海桑田之类的感慨。长辈们怀旧时,我眼前浮现的是:涌着白浪的河水穿旧村而过,河两岸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水声掩盖不住夜里的一片蛙鸣;充足温暖的秋阳下,河两岸翻滚的稻浪,闪着金灿灿的光……稻米饭的香气,猛然就在鼻翼间萦绕起来了。
水电站蓄水,祖辈的家园沉没在一片汪洋中。先辈开始在并不肥沃的坡田间耕作栖息。雨水再充足,无霜期少到可怜的高寒山区,怎能种出白白亮亮的稻米呢?
炊烟照常升起。袅袅升腾的炊烟,总也飘不上群山之巅。
被先辈称作冰沟的大山,十月中旬,高高的山顶就会呈现出雪的颜色。在那向阳的山坡上,安息着我的祖父祖母。那年正月,祥和的冬日阳光下,善良卑微的祖母,在冰雪中与人间艰难作别,就此和祖父作伴长眠。
通往祖父祖母安息地的山间小道,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寒风呼啸在身前。站在山坡上眺望小巧安静的村庄,童年往事历历在目。再看挺立在山坡上的祖屋,多么孤独倔强。祖父祖母的一生,如同经年的简装书,几乎都被装在了平实的民居里。空了多年的祖屋,仿佛还能听到祖父祖母的说话声和咳嗽声,燕子和麻雀早把这里当作了天堂。
呢喃的燕子,连堂屋棚顶上,都给垒上了玄妙的窝,不停从破碎的窗子飞进飞出。忽地一下,老燕闪飞进屋,贴落到泥巢边。拥挤在窝里的雏燕,立刻挣着脑袋,一个个把大黄嘴丫张到极限。祖屋显然不只有寂寞,还有燕子欢喜的吵闹声。
下山刚转过祖屋房角,伴随鸟儿的一声声惊叫,从破损的窗口惊飞出一群麻雀。拉开吱嘎作响的房门,走进屋内,在祖母曾经摆放花盆的窗台上,赫然躺着一个掉队的小家伙。我捧起它娇小的身体,柔软的褐色羽毛向我传递着生命的热度。我一下陷入心痛愧疚中。要是知道,屋里躲藏着娇怯的精灵,我肯定会让自己的脚步轻慢下来,那它就能和同伴一起,从窗口从容飞走。或许,它会在空中调皮地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甚至在空中得意地叫上两声。可结果呢,急促的脚步声让它慌不择路,撞上窗玻璃,晕坠在布满灰尘的窗台上。
我离开后,不知那只麻雀是否像从噩梦中醒来一样,在窗台上站起身,抖抖羽毛,振翅重回蓝天了?它能想到,我至今还为它牵肠挂肚吗?
身在几百里外的小城,当梦见翩翩少年奔跑在故乡的山野间,醒来总想沐浴一身晨光,回到故乡,好好端详开在春风里的马兰花以及崖畔上那片绚烂的映山红……
大好河山一隅,是我的故乡,她犹如温暖的大手,一直牵着我。她会在深夜里抚摸我眼角的细纹。当她将我紧紧拥入怀里的时候,我的心里便温暖如春,生长出蓬勃的希望。
(王齐君 单位:沈阳铁路公安局通化铁路公安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