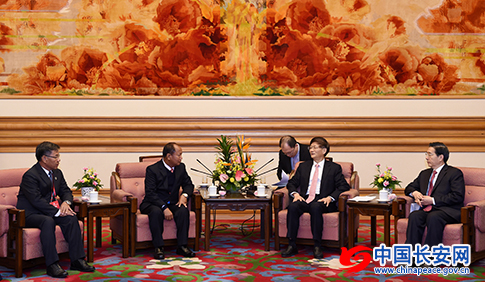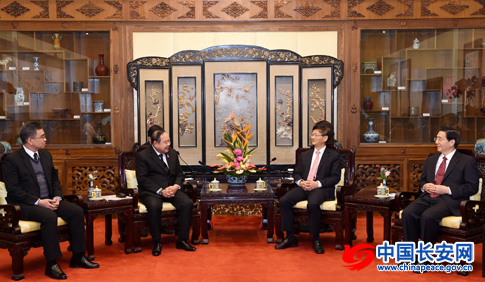入腊月,年味也就越来越浓了。集市上红彤彤的对联,金灿灿的福字,一张张炫彩缤纷的年画点缀着新年,它们如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般,缺一不可,否则年便失去了味道。
记忆中的年画,无论是“一团和气”“万事如意”还是“八仙庆寿”“年年有余”,都以各自的风情、不同的寓意自成画卷,无不体现着欢乐、祥和、幸福的味道。满墙的山水、花草、鱼鸟、人物好像把五彩的世界都搬进了家。年画中不仅有了人间烟火,还把更深更浓的精神血脉镶嵌其中。
逛集市、购年货、买年画、贴年画也成了各家各户过年时必不可少的一种习俗。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做豆腐……等准备好了这一切,年画也就粉墨登场上墙了。往往在大年三十这天,母亲拿来器皿,放入些许面粉,倒上适量水,在火炉上慢慢打成浆糊,我负责上墙,姐姐负责指挥贴年画的位置。我俩把山水画贴到墙这边,人物画贴到墙那边,明星人物贴太正不好看,斜着贴更漂亮,姐姐像指挥官一样有条不紊地安排着。
傍晚时分,母亲盛上一盘煮好的饺子,放到擦洗得洁净如新的灶台上,旧的灶王爷已经在腊月二十三上天言好事去了,灶王爷要换岗了,母亲摆好贡品,取出用木板水印制作的灶王爷画像,口中念念有词,虔诚的贴上墙,新请来的灶王爷坐在了灶台上方,注视着锅里的稀稠,感受着全家人一年中的冷暖,母亲说这叫聚灶。贴年画就像一场隆重的仪式,这是老百姓对好日子的期盼,是一年一度的愿景。
正月里,人们走亲访友时也不忘对各家墙上的年画评头论足一番。村北李嫂家贴的门神是秦琼和尉迟恭,一人手握双锏,一人手持双鞭,面容威严。还有的人家门神贴的是郁垒神荼,神荼位于左边门扇上,身着斑斓战甲,面容威严,姿态神武;郁垒位于右边门扇上,一袭黑色战袍,神情超然自逸。无论是何方神仙,都寄托了劳动人民一种消灾免祸、趋吉避凶的美好愿望。
村南王婶家的一组《夜读〈春秋〉》《红灯记》的年画让人过目难忘:画中的关公一袭绿袍,手抚长须,丹凤微闭,沉浸在《春秋》的世界里;画中铁梅和李奶奶手托红灯高高举过头顶,坚毅的眼神和为革命前赴后继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这几组年画,也让整个屋子熠熠生辉。如果说郁垒神荼的年画给予年幼的我是视觉震撼;那么《夜读〈春秋〉》《红灯记》的年画给予我的则是心灵荡涤。通过一张张年画,让我逐渐领略了祖国大好河山,风貌人情,启蒙了我对传统文化的痴迷,义薄云天、忠孝礼义的精神更是深深扎根在了心里。
时代在变,不变的是我们的情怀。一幅幅年画,是对新年的美好祝愿,是对生活的炙热期盼,也是对文明习俗的一种传承和认知。
(郭军峰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