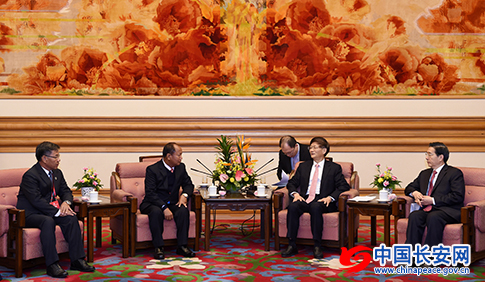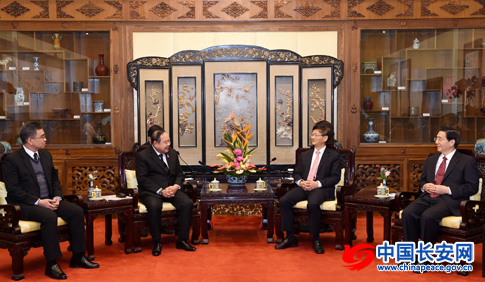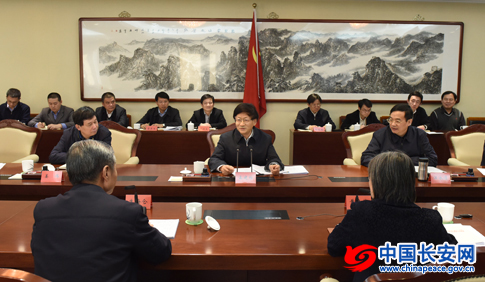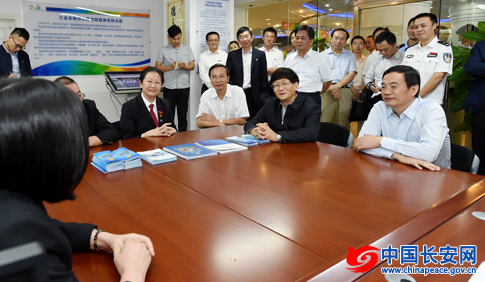《智囊》中的司法智慧
康民德
《智囊》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著名的说古方式记述、以启发人们智慧的文学作品和历史实录,系明代文学家冯梦龙于天启六年(公元1628年)辑录而成。冯梦龙在该书《自序》中强调了“智慧”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用于人,犹水行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坳则智满之。”可谓精辟之至。
从古至今,法乃国之重器,司法则为定分止争的终极载体,执掌法权者较之其他行业群体需要更为广博深厚的智慧,需要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纠葛中,具备透彻析理、利益衡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能力和智慧,在追求司法的实质正义的同时,还要切实和天理、国法、人情达到融会贯通。《智囊》所记述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个鲜活的智者群体中,也会让我们在其间领略到古代司法者身体力行体现出的令人钦佩叹服的、圆熟的司法智慧。
《上智部·通简》中记载有以下几例:
北宋时薛简肃镇守四川,一日于大东门外设宴,城内卫兵发生叛乱,但很快带头卫兵被捉拿归案,兵部督监禀报薛公,寻求惩处之策,薛公命将此带头卫兵当即处决,对其他叛乱者则不再追究。事后,百姓以为薛公之举决断英明,如果因此动用兵力抓捕,再施以严刑逼供同党,首先肯定数月内难以完结此案,且因此造成百姓人心惶惶,当地社会局面和治安必乱,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可见薛简肃是以公心为怀,如其稍稍裹带私心,为弄权而急功近利,借此捞取政治资本,则必会大肆搜捕,势必将涌现冤案,百姓也定会深受其害。操持法度过程中,一个智者理应从宏观全局考量问题,把握事态,“一操一纵,度越意表”,要善于在纷乱事态中处之以静,化繁为简。
西汉时的朱博系一名武官,对律法条文并不熟悉。在其担任冀州刺史职务(行使监察检核职能)期间,一日外出巡视到某县衙官署,遇数百名当地百姓和个别官吏聚集申告,小小一个官署被挤的水泄不通。朱博遂令官署佐吏明确告知申告者:凡反映县丞、县尉情况,因非刺史职权内务,可到郡守处反映;凡反映郡守及属吏情况,则到我办公处反映;有人被官吏冤枉或反映其他盗贼、诉讼等事宜可由各分管官员办理。数百人闻之纷纷散去。朱博办公治理依照层级流程、法定程序,有条不紊而令人信服,也避免了若盲目处置各类纠纷事宜,可能会受个人主观臆断及能力局限而引发不良后果。
北周文帝宇文泰在位时,韩裒担任北雍州刺史,该地盗贼横行,韩裒遂暗中进行了走访探察。随后,他召集州内一些狡猾且交际复杂的年轻人,委任于他们捕盗首领职务,并划分地段,由各自分头负责,并规定段内发生盗案不能抓捕盗贼到案,则对该段负责人以故意纵盗罪名论处。这些被委任的年轻人心下恐惧,遂纷纷揭发并落实具体事主。韩裒将举报名单收好并在州门发布公告:凡做过盗贼之人必须速来自首,本月内不自首则抓捕处决示众,将其妻赏于先来自首之人。不到十天,州内所有在册盗贼全部自首归案。韩裒应诺对这些盗贼罪行给予赦免,允许其改过自新,从此,雍州境内得以安宁,再无盗情。韩裒运用了极具智慧的治盗手段,借助民力及律法的威慑,最终达到了治理一方的目的。
明朝叶南岩任蒲州刺史,有一桩群殴案件告到他处,其中一人满面鲜血且身负重伤,脑袋开裂,生命垂危。叶公看后很是怜悯,并亲自给伤者捣药敷伤口,他还让官署内谨慎厚道的官吏看护伤者,并言明:任何人不得会见伤者,看护人务必要用心看护,如伤者死亡,则由看护者担责。他对打人凶手略加审问即将其关入监牢,其余人释放回家。有人问其缘故,叶公回答道:大凡争斗都无好气,此起纠斗中伤者如不及时救助必然伤亡,如此必要一人偿命,这就会导致一个家庭破裂,妻离子散牵连甚广。反之,伤者渐愈,打人者不过就是斗殴罪名而已,可以根据诉讼情况从轻处罚,达到惩戒教育即可。此事中叶公从大局着眼,不是简单武断办案,对民间冲突纠纷费心调停,不仅保全了当事各方及其家庭的稳定,也充分彰显出社会治理中司法的大智慧。
《明智部·剖疑》中则记载:后汉梁地某人的继母杀害了其父,该人遂以血还血地将其继母杀死,官府因此拟用大逆罪对凶手判罪处罚,孔季彦说:从前文姜同其兄齐襄公杀害其夫鲁桓公,《春秋》在记叙此事时不称姜氏而称夫人,《左传》说由于文姜与鲁庄公已断绝了母子关系,这种称呼符合礼数,断绝了母子关系即成一般人了。按照古人的标准,此人应以不经官府而擅杀有罪当杀之人来治罪,而不应该是判处大逆罪。人们均认同孔季彦的说法,也认为这是符合律法公正的。古往今来,司法的公正不仅仅体现为在实体层面对触犯法律之人的惩处,还应该高度注重程序层面的运用,法律实现其公正和权威的基础在于为人们所认同和信仰,法律在任何时候也需要通过限制司法官的恣意妄为,来保障司法的公平正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处罚罪名的适得其所何尝不也隐含着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价值?
《明智部·经务》中记载:北宋范纯仁曾担任襄州知府,该地风俗不事养蚕纺织,故少有人种植桑树。范纯仁感到忧虑,于是他对监牢中那些被判处轻刑的人予以释放,让他们戴罪回家种植桑树,按照其罪行的轻缓程度决定种植桑树数量的多寡,并按照其种植桑树的质量免除其一定的刑罚,从此桑树在该地产生了利益。曾背负罪名之人也因自食其力,重新融入社会。此举为百姓所称道。自古以来,法律具有止恶扬善的价值取向,法律规范并约束着社会群体的行为,同时,法律实施的更大价值在于恢复和调和社会秩序,进而服务政治、经济等各项社会事务的发展,范纯仁无疑深明此道。
《察智部·诘奸》中记载,明代周忱巡视江南时候,随身携带一个小本,每日将各类见闻以及天气、环境变化等都记录下来.起初人们并不理解。一日,某县主事报告周忱,境内发生了运粮船只被狂风吹走造成严重的物资损失后果。周忱遂询问当天发生此事的具体时间、风向等事宜,主事回答闪烁其词,颠三倒四,周忱利用手中每日记录的天气状况戳穿其谎言,主事只得认罪。恰如冯梦龙所认知的那样:智慧需要明察,才能显现出其效用;而明察若不以智慧为基础,则无以真正洞悉事物的精微关键之处。周忱在此事件中体现出来的智慧恰是来自其平日的用心、细致之举,给司法者的教益就是“非明不能察”,见微知著,明事理、知人心,才能明察秋毫、解难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