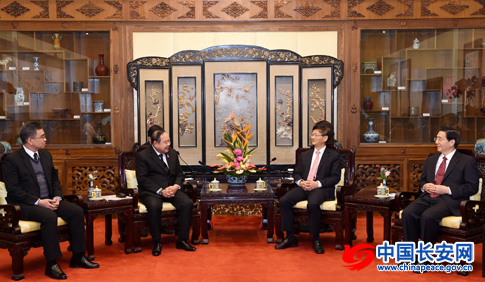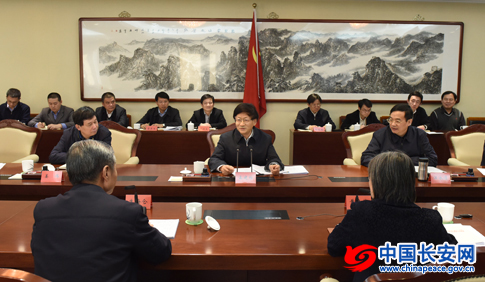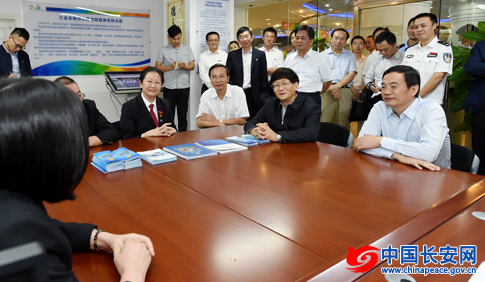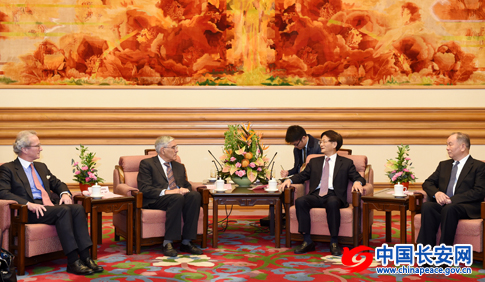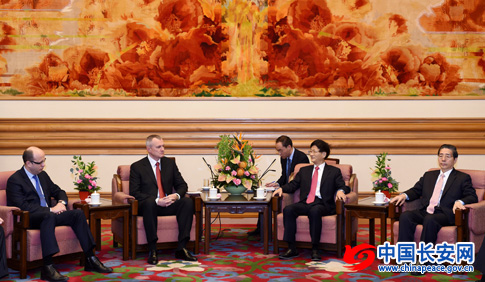我坚信,他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邹宁浩。
认识他,是在中国消防协会主办的一次展会上。作为《中国消防》杂志的骨干作者,他是新闻报道组的重要成员之一。那次,他给我的印象是羞涩和自信。
在主办方组织的座谈会上,轮到他发言时,他竟然一时语塞,不好意思地笑了。事后我对他说,你这扭扭捏捏的样子,哪儿像个当警察的啊。
活动期间,他换上了消防警服,说是要去采访。我说现场这么多游客,外国人就占了不小的比重,别在细节上影响了警察形象。他说警服穿习惯了,就该这样子出去转转,说完,还拍了拍身上的警服。事实证明,他是自信的,在展会现场他的回头率极高,那身橄榄绿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是一个普通的消防警,当过3年消防战斗员,而后就一直战斗在消防宣传一线。作为火场文书,他总是随警出动,第一时间出现在灭火救援现场,每次出警之后,别的战友休息了,他还在加班写稿子。
他不是科班出身,全凭自己的勤奋在宣传岗位上摸索,作为《人民公安报》浙江记者站的通讯员,他的稿子遍地开花,在《工人日报》《中国消防》等省以上媒体崭露头角。他的作品几乎涵盖了新闻体裁的所有类别,不论大事小事,在他笔下都成为鲜活的文字,那是属于他的阵地。
他会偶尔跟我交流工作上的体会,我总是怪他不肯用心去写一些有深度、有力度的作品。当时我固执地认为,在火热的消防警营中,有太多可以去深层次解读的新闻点。现在来看,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让他不得不陷于被动应付的窘境,这或许是基层消防新闻工作者共同的烦恼。
除了工作,他还会跟我聊一聊生活上的事情。他业余时间的爱好是收集消防邮票、车模和做公益,他的工资大部分用在了这上面。他在集邮方面还颇有成就,他说,每一枚邮票背后都有故事,承载着历史,我得研究研究,出个册子,将来也加入全国公安文联集邮协会。
有一次,他跟我说,他父亲当年初中文化,在消防当兵没机会提干,回到地方后,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说咱来年生个儿子再去消防,现在自己也当消防了,虽然只是个战士,但也有自己的事业,等来年也生个儿子,不信当不了干部。我说你说这么多,把我绕晕了。他憨厚地笑笑,说家里给介绍了对象,自己没时间去见面。我开玩笑说,不用娶媳妇儿了,搂着你的邮票过日子吧。他说我只喜欢跟消防有关的邮票,消防是我的职业,我的另一半应该理解和支持我。想想是这么个道理,我就不再拿他开涮。
今年初,他给我发信息,说支队打算帮他把发表的新闻作品结集印刷,免费赠送给读者,问我能不能给书稿提些意见。我说这是好事儿,就认真提了些意见。前些日子,他把书寄来了,简单浏览一遍,给他发微信开玩笑说有瑕疵。他问在哪儿?我说偏不告诉你。他连续给我发了几个尴尬的表情,那时候我被他逗笑了,因为我能想象到他因较真而着急的状态。
他对工作是较真的,经常为了赶写一篇稿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大半天,也时常为此不睡觉、不吃饭、不喝水。有时半夜他会给我发微信,问我是不是在加班写东西,我说是,他便发过来一个笑脸,说我在义乌陪着你呢。他时不时地提醒我别熬夜注意休息,我会反过来责怪他多管闲事儿,让他先管好自己,再说别人。但无论怎么说,我的心里还是温暖的。
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些温暖的话我再也听不到了,那个加入公安文联邮协的愿望成了他的遗愿。2016年12月16日,他的生命终止在某一瞬间,那瞬间也定格为我们不愿面对的永恒。
我在朋友圈里发了条微信,说实在不想说兄弟走好,我现在能做的只是为他写篇文章。与他相识的战友评论说,希望老大哥在文章里把我们的问候都带到,让他能听得到。
是啊,战友们希望那边再也没有火灾,让他好好休息。这是无奈的祝愿,更是艰难的表达。
但我坚信,他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邹宁浩。
(2016年12月16日,浙江省义乌市一公司发生火灾,义乌市公安消防支队宣传员邹宁浩在火场殉职。战友发现他的时候,他手里还紧紧攥着照相机。)
(初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