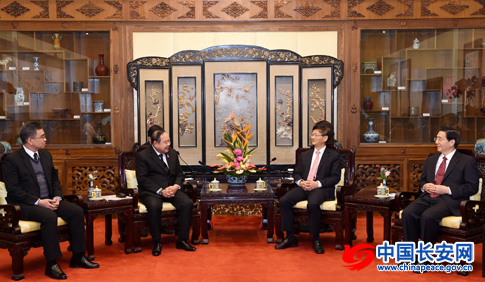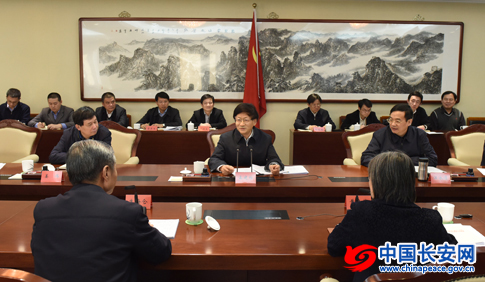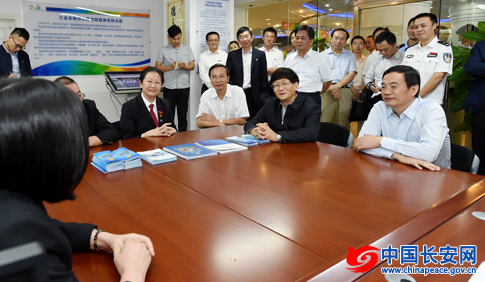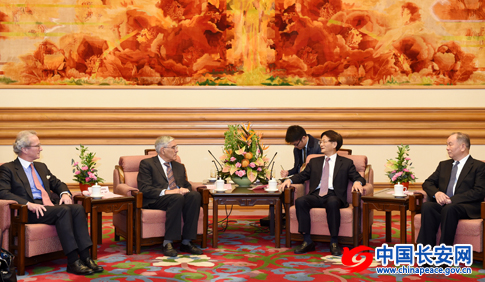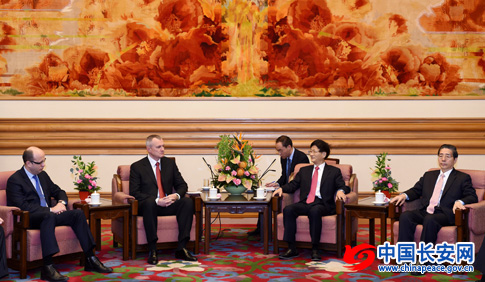郭躬,东汉官吏,从小就跟从父亲郭弘钻研法律,青年时期曾经给数百人讲授法律。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被任命为廷尉正,章帝元和三年升为廷尉。郭躬审理案件,“务在宽平”、“多依矜恕”,即能够以从宽为主,怜悯宽恕,能判轻刑者绝对不判重刑,反对违反法律滥杀无辜,因而受到皇帝的肯定和百姓的称赞。《后汉书·郭躬传》、《折狱龟鉴》等典籍上,记载他办案的几个小故事,读了颇受启发。
具体分析 不拘泥于表象
公元67年前后,奉车都尉窦固率兵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做他的副将。秦彭带兵驻扎在另外的地方,有时不经请示就依规杀人,窦固上奏皇帝说秦彭专权,擅自杀人,请求诛杀秦彭。汉明帝于是请公卿朝臣评判秦彭的罪行。郭躬因为通晓法律,也被招来参与评议。
朝臣们都赞同窦固的上奏,唯独郭躬说:“从法律上看,秦彭该杀那些人。”皇帝说:“军队出征,校尉要一律受制于主将。秦彭既没有斧钺,怎么能专权杀人呢?”
郭躬回答说:“校尉要一律受制于主将,那是说校尉与主将驻扎在一起,今秦彭另率一支军队驻扎于别处,和这有些不同,军情很紧迫如人的呼吸一般,有时不容许事先禀告主将后再作处置。况且按汉朝制度,棨戟就是斧钺,这样,秦彭的行为在法律上不算有罪。”皇上听从了郭躬的意见。
这个案件,从现象上看,秦彭确实有罪,其一,他不是主将,要受制于主将,凡事尤其是杀人更须向主将请示。其二,他没有斧钺。所谓斧钺是军法用以杀人的斧子,泛指刑戮,是军权的象征,一般为皇帝所授予。谁有斧钺,谁就握有生杀大权;当然没有斧钺,也就意味着没有生杀大权。
但是,郭躬却没有被上述表面现象所迷惑,对此案做了深入具体的剖析:副将受制听命于主将,那是指两人同住一地,而此案中秦彭是率军另驻他处;军情往往紧急,有时来不及请示,驻扎在他处的副将有权处置这些突发情况;有棨戟就等于持有斧钺,这是汉朝法律所规定的。所谓棨戟是有缯衣或油漆的木戟,官吏使用的依仗,出行时作为前导,驻扎时列于门庭。而秦彭就持有棨戟。如此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清实质的分析意见,皇帝当然会赞同。
注重证据 不凭主观臆断
又有一案,兄弟两人一起杀了人,但罪责不好归到谁的身上。汉明帝认为做兄长的没有尽到管教弟弟的责任,所以判哥哥重刑死罪而免除弟弟死罪。中常侍孙章宣读诏书时,误说两人判的都是重刑死罪。尚书上奏皇帝说孙章假传圣旨,罪当腰斩。
皇帝召见郭躬询问他的看法,郭躬回答:“孙章应罚金”。
皇帝说:“孙章假传诏书杀人,怎么说只罚金呢?”郭躬说:“法律上有故意犯罪和失误犯罪的区别,孙章传达诏书出现错误,事属失误,对失误者法律量刑要轻。”
皇帝又说:“孙章与囚犯同县,疑他是故意。”郭躬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
郭躬引用了儒家经典著作中的话。“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是说通往周京的官道平如磨刀石,路面笔直像箭杆。比喻实施刑罚应当如周道似的既宽平且正直,不应刻峻苛严;“君子不逆诈”则出自《论语》,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也不无根据地猜测别人不老实。郭躬引用儒家语言起到了援典以自重的作用,得出结论:君王以天为法,在议罪判刑时,不可以通过主观猜测,任意曲解,牵强附会,作出判断。皇上说:“好。”
这个案件涉及矫制罪,即假托君命行事,汉朝出现的罪名。唐代颜师古解释为“矫,托也,托奉制诏而行之。”用大白话说就是假传圣旨。此罪分三等,矫制大害,处腰斩;矫制害,处弃市;矫制不害,处罚金。“汉律规定,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任何犯罪都有故意和过失之分,矫制罪也不例外。
确定一个人犯罪的主观状态,要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要有证据予以证明,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是故意犯罪,就只能按过失犯罪来处理。此案中,孙章因一时疏忽读错诏书,显然属于过失行为。但皇帝又怀疑孙章与囚犯是同乡关系,有可能是故意报复陷害。这样的怀疑既不合逻辑,也没有道理,因为是同乡不一定就必然有恩怨。郭躬便依法依儒家经典给予一番解释和批驳,使皇帝欣然接受了不能凭主观臆想,就确定一个人主观故意与否的正确观点。
准确把握 不滥施以重刑
郭躬断案,务求宽容公平,审案判刑,大多喜欢同情宽恕。被任命为廷尉后,便写奏章,建议对四十多条量刑过重可以从轻论处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皇上批准后,所涉及的法律条文都得到修改并颁布施行。
汉章帝章和元年大赦天下,对在押犯减轻处罚一等,免死罪,也不加鞭笞,发配金城守边,但大赦令没有涉及那些在逃犯。郭躬上奏皇帝说:“皇上施恩给死囚犯减刑使其戍边,原因是重视人的生命。现在犯了死罪的逃犯总数不下万人,自从大赦天下以来,抓捕的逃犯很多,但赦罪的诏书没有涉及这些人,都判了重罪。我私下想皇上福恩应该浩荡宽宏,大赦令之前犯了死罪又在大赦令之后被抓捕的罪犯,都应不判死刑,不加鞭笞,发配金城,这样既保全了人命,又有益于边防。”
皇帝认为很对,又专门下诏赦免了这部分人的死罪。
郭躬之所以如此办案,与他具有渊博的律学知识分不开。所谓律学,是指根据儒学原则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释的法学,从文字上、逻辑上、法理上,对律文进行阐释,多是以私家形式进行。如西汉的于定国、杜延年,东汉的郭躬、陈宠等人,世代传习法令,收徒教法。东晋以后,这种私家注释逐渐由官方注释所取代。
《郭躬传》载,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汉武帝时期担任廷尉、御史大夫的杜周与其子杜延年,都明习法律,并有律学传世,人称杜周的律学为“大杜律”,杜延年的律学为“小杜律”。郭弘研习的就是“小杜律”,郭躬子传父业,也精通“小杜律”,对法律有着精湛的理解和深刻的把握,深知维护法律尊严的重要性,所以敢于依据律文而向皇帝直言相谏,甚至于展开多轮辩论,以收到按法断案的最佳效果。
对郭躬断案,史上评价甚高。《后汉书·郭躬传》载,“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夫不喜于得情则恕心用,恕心用则可寄枉直矣。”“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狱必察焉。原其平刑审断,庶于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议物,舍状以贪情,法家之能庆延于世,盖由此也!”
曾子语出自《论语》“子张第十九”,意思是说,在上位的人不依规矩行事,百姓的心早就涣散了;你假若能审出罪犯受屈犯法的真情,就应该可怜、同情他们,不要因为明察而自鸣得意啊。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有宽恕之心,才能公平断案。郭躬就是这样的人,能够设身处地的体谅他人,宽厚仁爱,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探求真实的情况,忠诚尽职。南宋郑克所著的《折狱龟鉴》,也将评价郭躬办案的两句话“推己以议物,舍状以探情”奉为经典,在其他案件中多次引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左连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