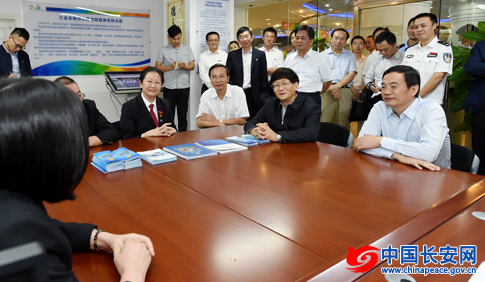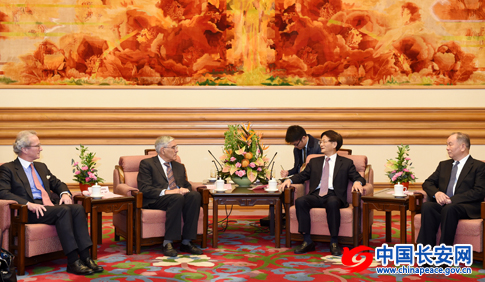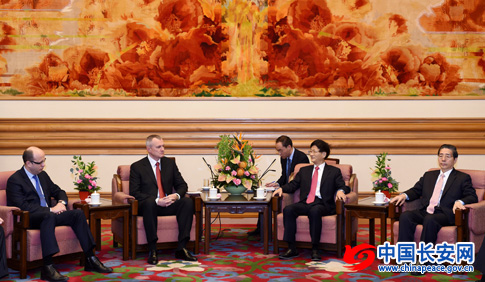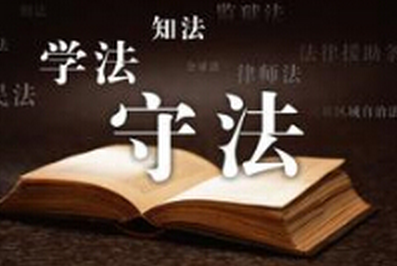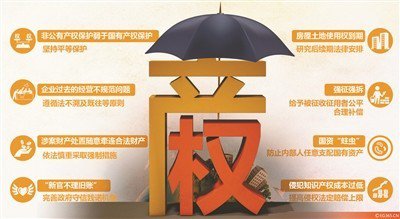依法治善:打造互联网公益净土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来,我国社会捐赠总额从2006年不足100亿元发展到目前1000亿元左右。然而,互联网公益慈善的高速发展也伴生着不和谐的音符:“公益明星”挪用慈善资金获刑;网络主播搞“假慈善”沽名钓誉;网络大V一人分饰三角,骗取网友爱心款被警方逮捕……人们急切盼望净化互联网公益慈善,还爱心一片净土。
假慈善防不胜防
“当前互联网公益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互联网平台众多,良莠不齐;二是互联网筹款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甄别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成都市慈善总会秘书长荣道清说。
11月3日,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人民法院对一名“公益明星”作出了有罪判决。凉山汉达社工服务中心法人代表闫伟杰,将单位代为管理的财务款64790元非法占为己有,挪用慈善资金10万元。这位被称为“义工李白”的“公益明星”,曾在众筹平台运营“给凉山代课老师补贴”项目,短短5天时间就筹集了141万元善款。正是该项目中的宣传与事实不符,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此前,他还在“乐捐”平台上发起了20余个筹款项目。由于被捕,多个项目无法继续执行。
广州市慈善会秘书长汪中芳认为,互联网让个人求助的实现变得简单,而且突破了传统的邻里互助模式,具有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性质。但如何防止个人求助的信息造假和骗捐的出现,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今年1月,江苏苏州市公安局民警在知乎网浏览时发现,网民“ck小小”发布了题为“长期被疾病折磨,选择自杀是最好的方式吗?”一帖。帖中自称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堪疾病和生活重负想要轻生的女大学生,并公布了自己的支付宝账号。
经过调查,警方发现“ck小小”的真实身份为安徽籍男子童某。童某交代,自己先注册“小言”“童瑶”两个知乎网账户,通过互相发帖和回复,并盗用其他网友照片作为头像,虚构出“童瑶”这个毕业于复旦大学、高智商、高情商的“知乎女神”。在拥有一定粉丝数和网络影响力后,童某又注册了“ck小小”,自称患重病以骗取网友捐款。为增加可信度,童某通过“童瑶”账号发布了“已到医院探望过ck小小并当场捐助现金”的帖子。在“女神”的引导和示范下,越来越多网友向“ck小小”捐出善款,累计捐款24万元。
除了利用网络平台直接“骗捐”,假借公益之名沽名钓誉、骗取钱财的现象在一些新兴互联网平台上也悄然滋生。前不久,一段名为“揭秘大凉山公益作假”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经查,直播平台“快手”上涉嫌搞假慈善的主播超过10人。
互联网公益慈善的掣肘
互联网公益慈善的低门槛、便捷、高效等特点让慈善更加开放化和大众化,但质疑之声仍不绝于耳。捐赠的钱会完全到受捐者的手中吗?谁在管理这些资金?用什么样的形式去托管资金?正因为互联网公益慈善的广泛影响力和高参与度,使得公众对“瑕疵”的容忍度更低。
采访中,多位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表示,骗捐、诈捐、假慈善等行为是对公众的欺骗和对爱心的肆意践踏,极有可能造成公众对真慈善、真公益的误读,破坏慈善生态,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恶果。
“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业缺乏制度和监管,为不法分子留了可乘之机。”成都一位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说。相对官方公募而言,互联网募捐平台有两大短板:一是难以对相关信息逐一把关,一旦虚假信息进入,就有可能引发诈捐情形;二是传播迅猛,诈捐信息发布后善款往往难以追讨。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发布的《透明宝典——中国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指南》显示,2015年和2016年中国的慈善透明公众满意度均为56%,公众的感受尚未达到“及格线”。
早在2014年,李克强总理就提出要增强慈善组织公信力,把慈善事业做成人人信任的“透明口袋”。今年9月起正式实施的慈善法也规定,公益机构应该公开各项目的账目等,推动公开、透明成为公益组织、机构和单位等的重要标签。互联网公益慈善在这方面仍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互联网公益,最主要的是互信的问题。“在国外,很多人认准的是机构,而不是项目。他信任你这个机构,就会相信你发起的项目,这是捐赠人最理想的状态。”爱德基金会爱德荟众筹项目主任方峻说。
依法治善任重道远
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应当在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最终,包括腾讯公益、公益宝、轻松筹和广州市慈善会慈善信息平台在内的13家网络募捐平台获得认证,这意味着网络慈善进入“固定入口、统一监管”时代。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昕杰认为,民政部以官方认证的形式为网络募捐平台设置了准入门槛,不仅可以将资质较差的平台挡在门外,压缩诈捐骗捐的生存空间,还能为资质良好的平台推广其形象,提升公众对网络募捐的信任。
与此同时,以轻松筹等为代表的网络筹款平台仍面临诸多问题。成都志存律师事务所主任李苗指出,依照慈善法的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由该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并管理募得款物。但是,个人救助不适用该法。
“当前,一些个人利用了个人救助这种‘法律不禁止、慈善法不调整’的灰色空间,轻松绕过了监管。”李苗说,“平台并没有对个人救助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对捐助款的使用也没有严格的监管,极易导致个人虚假求助有恃无恐。”
虚假的个人求助金额一旦达到一定标准,其行为将涉嫌构成诈骗罪,但对于募捐平台是否也应对虚假求助承担责任,现行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李苗建议,慈善法在修改完善时,可以借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督促平台严格履行审核监督义务。
格桑花西部教育救助会副理事长徐来说:“尽管公益已逐渐成为社会和生活的一部分,但公众需要提高辨别力,主动追踪和监督善款的去向。”
“公益组织的自律也很重要,有时候因为疏忽和管理不善引起质疑,结果影响了品牌的公信力,非常不值。因此每个公益组织应注重规范,加强内部管理,发生质疑后要积极回应。”成都市义工联合会理事长苏世杰说。(吴光于 邱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