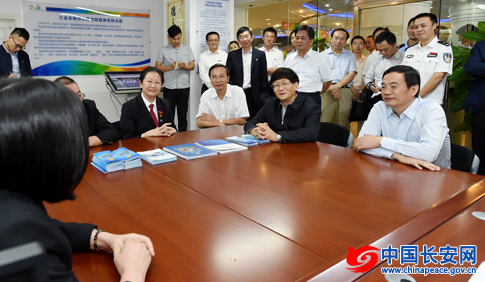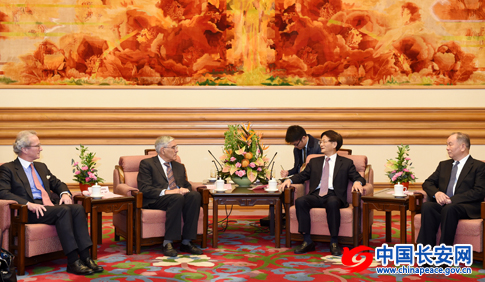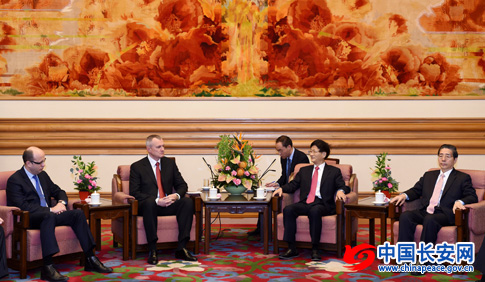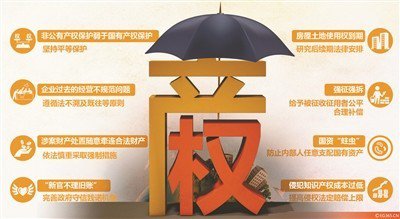图为电影《盛先生的花儿》海报。
从研究生入学第一课起,著名导演、我们的老师谢飞就一直追问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课堂里的每一个人:你们要做什么样的电影?
我最终交出的答卷是《盛先生的花儿》。
其实,我最初是想呈现一个关于“充气机器人的爱情”的作品,但后来觉得作为毕业作品,实在有违学院派的庄重。再加上近些年,94岁高龄的外公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我潜意识里想要做一个跟他有关的作品,于是发现了旅美著名华人作家哈金的短篇小说《养老计划》。
跟哈金老师的联络颇有意思。辗转得到他的邮箱,试着写了一封信,没想到真的收到了的回复。初始,他信里讲,听好友余华说,国内影视改编权的价格大约20万起。后听我说是学生作业,作为波士顿大学中文教授的哈金二话不说,以几乎零改编费给了我,此是我最初的动力。
剧本完成到数稿之后,我们开始琢磨演员的人选。其中主人公“棉花”的确定,似乎非常顺理成章。辗转把剧本递到颜丙燕的手里,很快就有了一次和她的见面。她因为喜欢剧本和人物,所以也愿意演,且豪气地表示:知道你们没钱,没钱也演。之后,王德顺、艾丽娅等戏骨,也在看完剧本后依次就位。
此时恰逢学院“新人成才计划”启动,剧本在谢飞老师的推动与数次评选中,得以脱颖而出,获得制片厂投拍及支持,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又有民营电影公司对剧本青眼有加,与制片厂联合启动了这个片子。
《盛先生的花儿》这部电影的命运,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毕业长片作业走到现在,从成片那日起,由多舛变成了顺风顺水。这其中的转换缘由,作为创作者,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只知道,一心挣扎向前,管它逆水还是陆上行舟。然而,现在想来,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从来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孤独。
由于面嫩,常被视为二十岁的人。当时决定拍摄这样一部关乎死、关乎生的电影时,更是引人疑惑。彼时它还是一篇极短的短篇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唐人街。
于情于理,我们必须把它拉回中国北京当下——这个地球上,我心目中最合适发生这样千回百转、复杂因果、爱恨交织故事的地方。这是盛世华年,这是最好的时代,丰富绚丽、璀璨夺目,却又躁动不安、浮光掠影。
选择一个最微小的切口,进入我们的电影。那就是,一个衰败失智却又似乎洞察一切生命真相的老爷子盛先生,和沃土一样丰盛却又茫然无着的女人的故事。全片贯穿着死,以老人的最终离世为主要情节线。同时,又暗含着生,新的生命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降临,这是全片的隐线。
这个故事其实关乎着现世的、触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安全感”缺失。而这种缺失,在片中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有体现。
女人棉花来自农村,在转型成为城市人的路上,因为生育问题,她有着不稳定的婚姻与恋爱关系;盛先生的“不安全感”更复杂,它来自于历史创伤、情感创伤、亲子关系;盛先生的女儿来自于无爱的环境,她充满疑虑,担心阶层下降、财产受损……
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何尝不是社会心态的缩影。安全感缺失,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管理者而言,都是具有警示意义的。值得思考的是:如何从制度层面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电影的话外之音。
(作者:朱员成 电影《盛先生的花儿》导演、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