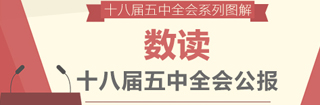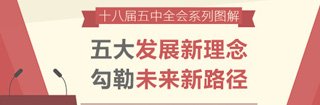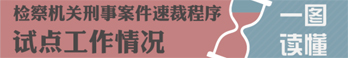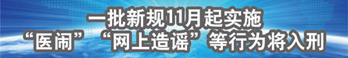上海召开第24届中国犯罪学学会学术研讨会
网络色情交易“O2O”犯罪现场呈现虚拟化
移动互联网时代“黑色产业链”呈爆发性增长态势,专家呼吁各方协作堵网安漏洞

中国犯罪学学会第24届学术研讨会现场。
叶先生最近玩得很嗨,每到晚上总是在微信群里和其他几个群友“小来来”,一起玩发红包、抢红包的“游戏”,比如将50元钱分成5份,谁抢到最多,谁就必须发下一个50元红包。因抢红包金额有随机性,十轮八轮玩下来,群里有输有赢,大家都感觉很刺激。
但是,最近叶先生听说他们这种行为可能有赌博的嫌疑,因为有人因此而被刑事拘留,原来认为“小来来”的叶先生不敢再玩了。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在创新,犯罪形态也在更迭,继QQ之后,微信也不再是一潭清水,早已经成为一些不法分子犯罪的温床。有人借助微信平台招嫖,有人在微信群里赌博,有人还打着低价代购的名义销售假货……
在11月7日上海召开的中国犯罪学学会第24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和专家就移动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一些新型违法犯罪展开探讨。与会专家认为,有必要加强网络安全投入和研究,完善网络技术,堵塞网络漏洞;加强政府部门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大力发展网络安全产业。
现象
“黑色产业链”呈爆发增长态势
就在2015年10月上旬,上海警方公布一起微信红包赌博案,犯罪嫌疑人利用微信抢红包发放钱款数量随机性的特点,组织微信群内成员轮流发红包并抽头营利。
公安部门侦查发现,年轻女子单某利用自己的微信账号,建了一个名为“面膜288一盒4片”的微信群。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售卖面膜的微信群,但单某等人通过发红包、抢红包组织群内成员进行网络赌博,并从中抽头营利。
所谓游戏规则是:每次由“代包手”准备288元资金,单某某等组织者抽头28元后,剩余260元分成4份,供玩家抢红包。抢到红包金额倒数第二的为输家,必须支付给“代包手”288元作为下一轮抢红包的活动本金。
截至案发,群内成员最多时超50人,平均年龄26岁左右,发红包数量累计500余个,涉案金额10万余元。警方抓获单某等8名涉案犯罪嫌疑人,缴获涉案手机6部。
警方说,由于作案手法简便、隐蔽性高、流动性强,以微信发红包、抢红包形式开展的赌博活动危害性甚于传统赌博。
在中国犯罪学学会第24届学术研讨会上,腾讯研究院犯罪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法学博士陈琴说,如果说互联网时代使得传统犯罪从现实社会拓展到网络空间,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则促进了网络犯罪的空间拓展,现实社会向网络空间然后再向移动网络空间的犯错拓展。
陈琴博士说,相较以往,2014年互联网犯罪呈现出犯罪空间从PC向智能移动终端加速转移;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趋势进一步凸显;利用伪基站实施的犯罪数量飞速增长;针对境外目标、利用境外设施的犯罪明显增多;犯罪的针对性和欺骗性大大提高;新的犯罪手法和犯罪趋势不断涌现等六大特点。
网络黑色产业链已经呈现低成本、高技术、高回报的爆发性增长态势,对网民造成了金融资产和个人信息安全等多方面的危害,成为阻碍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因素。
案例
网络色情交易借助“手机支付”
陈琴博士向与会人士介绍了2015年9月浙江宣判的一起首例微信传播淫秽物品案,说明微信除了为广大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之外,也让某些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这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微信私密性强、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等特点实施新型违法犯罪,而其中尤以网络诈骗、侵权、卖淫嫖娼、赌博等为多见。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张某在担任一微信群群主期间,放任阮某等人在群内发布淫秽视频累计达451个,其中,阮某个人发布的视频数就达76个。
张某身为群主,有权限把任何一个群员强制踢出该群。他辩解称,因阮某上传淫秽视频而把他踢出过这个群,但群里的人又把他拉了进来,之后张某就放任不管了。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阮某在微信群内传播淫秽视频76个,已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张某虽未上传淫秽视频,但作为微信群的群主、管理者,并且群成员达57人,张某也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淫秽视频的主要上传者阮某及该微信群群主张某均犯传播淫秽物品罪,各被判处拘役一个半月。
陈琴博士说,网络色情呈现线上线下结合的趋势,即现在流行的讲法“电子商务O2O模式”,将线下色情交易的机会与互联网结合在一起,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台。这样的传播方式越发隐秘。
另外,一些不法分子借助网盘、云存储等新兴网络储存技术,将储存资源放到云上供人存取。使用者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通过任何可连网的装置连接到云上方便地存取数据。
“一些网络色情最终的利益链条都是通过手机支付来形成的,也就是说双方的交易不再使用现金,而是通过手机这种移动终端来完成”,陈琴博士说:“对从事网络色情交易的人来说,通过手机支付资金更加方便,也不容易被查找到。”
分析
仿冒欺诈账号55%来自广西
2014年腾讯雷霆行动通过开放黑产数据库和大数据分析能力,与全国警方及互联网合作伙伴建立多层次联动机制,全方位打击网络黑色产业链。
据公开报道,110.qq.com反诈骗举报平台共收到举报信息250余万条,协助各地警方侦破网络欺诈案件200余起,抓获犯罪团伙嫌疑人700余人。
腾讯社交产品累计封停打击违规公众账号8.5万个,拦截各类恶意营销广告、恶意链接500万个。在打击网络色情上,处置LBS服务3000万次,删除淫秽色情及招嫖类信息500万条。
就在中国犯罪学学会第24届学术研讨会上,陈琴博士公布了腾讯通过大数据分析,微信仿冒欺诈的不法人员地区分布,经对被封账号检测发现,仿冒欺诈账号55%来自广西,8%来自江苏,7%来自广东。微信仿冒欺诈的案件正呈高发趋势,单笔近百万或上百万元的欺诈案件陆续发生。
从上述发生的微信诈骗案件中,以冒充熟人类和冒充BOSS类最多。微信仿冒欺诈关系链获取的主要方式为:1、通过QQ盗号来盗取好友列表及备注情况2、手机木马拉取用户手机通讯录及短信内容;3、诱骗企业HR非法获取公司通讯录。
腾讯公布报告说,网络黑产犯罪团伙已经发展为跨平台、跨行业的集团式经营运作,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毒瘤,政府、警方、各大互联网企业、银行、运营商和第三方安全机构等应尽快建立有效的合作与共享机制,从源头上遏制网络黑产的生存空间。
根据《中国互联网犯罪形式及趋势分析报告》,我国互联网行业安全面临入侵数据流动链薄弱点对数据资源的破坏,违法和不良信息内容对网络舆论环境的冲击,以及不当使用数据行为对行业秩序的冲击等“三大威胁”,且安全事故具备明显的三个特征:
一是我国数据安全事故呈现安全威胁动态多元、范围跨领域跨疆域渗透、威胁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演进态势;
二是违法与不良信息内容产生新问题,其表现为不良信息转移至移动端、色情产业形式升级、暴恐内容多点散发形成跨域影响力;
三是不当使用数据行为冲击移动支付和电商的正常生态。
呼声
发展网络安全产业刻不容缓
网络犯罪作案时间短,空间跨度大,犯罪成本低,收益大,取证难,这些特点使得网络诈骗井喷式发生,而案件的侦查却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一些案件中,受害人只知道对方的银行账号或者QQ号等,而实施犯罪所用的银行帐户或者QQ号一般不是犯罪人通过真实身份办理的,这对侦破案件形成了难题。
在中国犯罪学学会第24届学术研讨会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任彦君认为,由于网络犯罪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犯罪现场跨越了物理与虚拟两大空间,使得证据的收集或者侦查较为困难。另外,被害人也会存在不报案、报案不及时、不知道保存相关证据等情况,这些都给公安机关侦破案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又加上一些基层公安机关存在技术瓶颈或警力不足的情况,使得公安机关调查网络犯罪存在畏难情绪和推诿现象,这导致犯罪黑数(指一些隐案或潜伏犯罪)的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犯罪气焰。
任彦君博士透露,相关网络犯罪属于高技术、智能化的犯罪,犯罪人一般有较为熟练的网络知识,他们懂得相关技术规程、如何利用系统漏洞等犯罪技能,并且懂得如何制造假象、毁灭证据来规避侦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无论公安机关在网络侦查人员的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方面,都不能满足网络犯罪案件及时有效侦破的需要,这削弱了对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导致了我国网络犯罪的侦破率不高。”任彦君博士说。
网络监管机制决定着网络的安全性。网络监管不仅是预防网络犯罪的基础,也是案件侦破的保障。任彦君博士认为,要探索建立以安全监管为主线,包括资源、运营、内容以及终端等各方面监管的分层监管模式。对于国家制定的安全等级制度、互联网备案制度以及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等制度要认真严格地执行。对于互联网审批的多部门管理进行输理,分清权力和责任。另外,对于银行卡、电话卡的申办管理,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温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副大队长林君和温州医科大学讲师刘婷在中国犯罪学学会第24届学术研讨会上递交论文《“互联网+”时代电信(网络)诈骗实证解析与综合治理研究》,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用了金融、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社会危害大,远远超过了传统犯罪,造成的严重后果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破情况,未来趋势和滋生出来的犯罪活动“产业链”,已成为老百姓防诈骗的最大隐忧。
他们认为,电信诈骗犯罪防治工作已不能简单地套用公安四宝“打、防、管、控”来处理,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公检法司、银监会及各大银行、通管局及各大电信运营商、淘宝、QQ、微信及各类新兴互联网公司等多个部门、各个层面。
针对网络安全,陈琴博士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在创新,犯罪也在更迭,与此相应,我们在防治和打击移动网络犯罪时更需要将技术与法律融合,多部门相互配合,共守移动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秩序。她建议,有必要加强网络安全投入和研究,完善网络技术,堵塞网络漏洞;加强政府部门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大力发展网络安全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