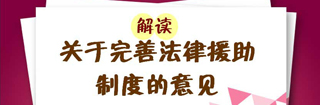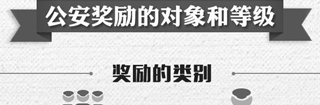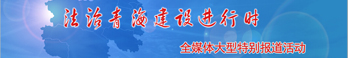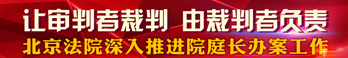张轶民:“舍”与“得”皆因为心疼

对42岁的张轶民来说,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安贞活动站是他生命里的一处烙印。2013年1月,他告别公安部的机关大院,前往安贞活动站出任站长,从此成了70多位离退休老人的“管家”、“小友”和“孩子”。
在此之前,他从未与这么多老人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在此之后,他再也舍不得离开这群老人。
他说,表面上,是他赢得了这群老人的心,其实,“是老人们让我动了情”。
凭借扎实的基本功通过一场场的“观察”
“我一直在观察你。”当83岁的韩缉熙说出这句话时,张轶民已经当了6个月的站长。
“观察”,是初来乍到的张轶民面对的第一道门槛。
韩缉熙是老刑侦,经手的案件与公文不计其数,眼光之锐利,做事之认真,在整个安贞站是出了名的。老人对张轶民的“观察”,止于一幅数十年前的字。
韩缉熙喜欢书法,公安部的大楼里有他多年前写的一幅字。张轶民偶尔路过,见到落款眼前一亮:“这不是我们站的韩老吗?”于是随手拍了下来。后来有一天,他陪着老人们聊天,韩缉熙兴之所至聊起书法。张轶民顺手把手机里的照片给韩缉熙看,没想到却让老人大为感慨:“几十年前的东西了,难为你还找得到。”
老人就此成了张轶民的忘年交。张轶民策划的每一个活动,他都是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基于几十年工作经验提出的建议,更是让张轶民受益匪浅。
但张轶民心里清楚,他面对的,绝不只是这一场“观察”。
2002年建站的安贞活动站,下辖安华西里、东土城、208监区等4个支部。站里服务的70多位公安部离退休老人,大多阅历丰富,不少甚至是公安部刚组建就加入的老人。他们人生经历丰富,要想通过他们的“法眼”,并不容易。
58岁的王福琴性格爽利,是208监区支部的活跃分子,张轶民陪她走访过许多老人的家。每路过一家,她都会被张轶民“惊”一下。她说,知道老人的家庭情况不稀奇,可是“他连谁家的孙子几岁,在哪上学在哪上班,统统说得比报菜名还顺溜”,这就让她不得不服了。
但张轶民告诉自己,这不过是身为站长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他说,要是连老人家里的基本情况都记不住,怎么可能开展好后面的工作?
用细心和耐心满足老人的诉求
年过八旬的公安部老干部董春岚,独自和有精神疾病的女儿住在一起。每次有人去她家,她的女儿都会阻拦,有时甚至还会破口大骂。这让很多人不敢登门。
张轶民却喜欢去,三天两头地去,被骂得满脸通红也去。不仅仅因为董春岚是他的服务对象,也是因为,“我看着心疼。”张轶民说,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到了享福的年纪却还得惦记着照顾孩子,“日子过得太苦了”。
去得多了,董家女儿慢慢不骂了,后来,她还主动和张轶民聊天。再后来,她甚至主动给张轶民打电话,提出要去医院看看病。发病这么多年,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张轶民赶紧帮她安排住院事宜。
治疗之后的董家女儿基本恢复了正常。令董春岚老人日夜揪心、以泪洗面的心事,终于可以渐渐地放了下来。
2015年5月2日,董春岚老人安然离世,所有后事,她的女儿都处理得井井有条。
这井井有条的背后,是张轶民的事无巨细。老人辞世前一天,正值五一小长假,张轶民从堵成一锅粥的高速一路赶回,6个小时路程里不断的电话和后事期间的关心,是给深受打击的董家女儿最好的定心丸。
在外人看来,连精神病人都能“搞定”的张轶民,一定是个口才惊人、见谁都能说两句的“自来熟”。但事实上,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如果旁人不主动说话,他几乎可以安静地坐一整天。
因为他的安静,不少人曾经对他在安贞站的工作有过一些担心。但他做得出人意料的好。2014年底年终考核,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组织对全部工作站进行测评,老干部们匿名打分,张轶民所在的安贞站高居第一,接近99分。
张轶民喜欢用“心疼”来形容他对这群老人的感情。心疼他们在人生路上的风雨,也心疼他们人到晚年后的各种无能为力。
因为心疼,他会绞尽脑汁发掘每位老人的兴趣点,陪他们聊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因为心疼,他愿意奔波数月,请老人们所有的儿孙为老人录一段生日视频,只为了圆老人一个全家团聚的梦。
张轶民说,正是因为自己的内向,让他更多了一份细心和耐心。他很少着急,即便是老人再糊涂的表达、再啰嗦的话语、再细微的诉求,他也愿意一直听下去,然后默默地尽力去做。“对老人来说,倾听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实现就更是一种满足。”张轶民说。
除夕夜离家返京为离世的老干部奔丧
今年2月18日,大年三十,人在沈阳老家的张轶民有些坐立不安。78岁的丁广荣老人从去年2月起就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他的病情,是令张轶民坐立不安的根源。
从踏上火车那一刻开始,他每隔几个小时便会给丁广荣的老伴王正荣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因为担心鞭炮声太响盖住了电话铃声,他还将自己爱人的手机号也给了王正荣:“万一我的电话没人接,你就再打这个电话。”
2月18日19时46分,他成了除丁广荣家属之外,第一个得知老人离世噩耗的人。几乎是第一时间,他翻出了手机里早就收藏好的、当天沈阳到北京的列车时刻表,买了最近的一趟火车票,踏上了返京之路。
没有人舍得他走。他的父母身体不好,手术都做过好几次。春节是他难得可以回家尽孝的时刻。这次自己踏着除夕的钟声离家,父母会是怎样的心情,张轶民不敢想。
其实他也可以不走。早在离京时,他的同事就已承诺,一切都有他们,让他安心回家过年。但他最终还是踏上了离家的火车。那是一晚完全一个人的大年夜,他从一场生离,奔向一场死别。
次日清晨,当看到张轶民出现在老人床前,王正荣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张站长,就是亲生儿子,也不一定做到你这样啊!”
衰老、病痛、死亡……对张轶民来说,从他成为安贞站站长那天开始,这些沉重的词语就成为他和同事们必须面对的常态。“老人把生老病死托付给你,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
为了这份信任,他们需要比一般男人更孔武有力。老人们大多住的是旧房子,电梯间和房间狭小,一旦发病,担架很难上去,全靠张轶民和同事们一路背上背下。王正荣至今记得,当一米八几的丁广荣压在张轶民的背上时,张轶民那憋红的脸和紧咬的牙。
有时候,他们又需要比一般女人更温柔体贴。病中的老人容易情绪化,亲人去世后的家属更容易情绪失控,需要有人一直倾听他们的伤痛,直到他们平静下来。
有时候,他们还要精于算计。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副局长王平一直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为了用固定的金额买到更优质的花束和更合适的慰问品,张轶民常常一跑就是好几个超市,更是京郊各大花卉市场的常客。“事情怎样都是做,但像他这样不惜时间精力,大事小事都替人着想的,不多。”王平说。
离职不离岗,一切为了“尽力”
今年5月,张轶民申请辞去安贞活动站站长一职。
这是一场“古怪”的辞职。
他坚定地申请辞任——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局长毕晓明再三挽留,但张轶民态度坚决,“站长这份工作分不得一点心,我不想占着位子,却又做不到。”
他又坚持着不肯离开——离退休干部局原本决定将他调至离他住处最近的木樨地工作站,他却说:“对那些老人们都有感情了,还是让我留在安贞吧。”于是现在,他成了安贞活动站的一名调研员。
站长之外,张轶民的另一个角色,是父亲。
因为先天性的原因,他的孩子发育相对迟缓。张轶民几乎将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都倾注到了孩子身上。大多数的工作日中午,他都会驱车将孩子送往南城的康复中心,然后再赶回来上班,下班后再把孩子接回家里,周末更是几乎泡在了康复中心里。
这场“古怪”的辞职,对他来说更像一场情感的拉扯。他一面揪心着下一代人不可知的未来,一面却又放心不下上一辈越来越需要人照顾的现实。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将是一场持久战。“不管结果怎样,我自己总要尽力。”他说。
张轶民对“尽力”的定义,远比一般人严苛。不是没有人劝过他,当站长和照顾孩子并不矛盾,好不容易取得的成绩,不要轻易放弃。但对张轶民来说,站长的意义,是更多的责任和尽力,而非所谓的成绩和名利。
老人们对名利的淡泊和对原则的坚持,是张轶民下决心辞任的根源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刘瑞珍老人,由于1949年9月份工作变动,导致她档案中的工作时间被错误地记录为1949年10月。30多年后,尽管她当时负责人事工作,也有可能找到证明人证明她实际的参加工作时间,可她却坦然接受了退休干部的身份:“现在这样就很好了,不要再给组织添麻烦了。”她说。76岁的张佳良老人,走路都不大利索,却可以为了党的一项决策和他人一争论就是一下午。张轶民说,当站长这几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老人,“我只有尽力向他们学习”。
事实上,老人们比谁都理解他的决定。“谁不是为儿女操碎了心呢?我们都盼着他和孩子好。”老人们说,“只要他还在,就好。”
张轶民的回答是:“我当然会在。我怎么舍得不在?”(周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