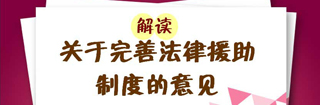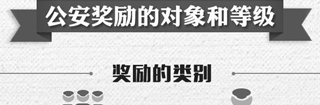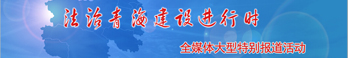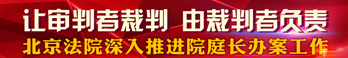家乡有扇敞开的门
似乎是摩天大楼鳞次栉比和车水马龙的城市气息让如今的城里人染上了一种特殊“文明病”。看那让人目不暇接、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防盗门、保险锁、那警惕的“猫眼”。难道真的有这么多的坏人吗?由于工作的异动,我搬入现在的住房快五年了,同楼层仅三户,邻里之间,门近咫尺,除了电梯间的偶遇外,却始终不知 “庐山真面目”,更谈不上姓氏名谁了。前几日,小区一业主大白天失盗,令人不思议的是犯罪分子在撬门扭锁时,邻人已发现动静,却竟以为是主人丢了钥匙,没有丝毫警觉,直至案发后才有所醒悟,啼笑皆非之余,我想起了家乡那一扇扇敞开的门。 我的家乡位于邵阳市东北望云山脚下,那时候,家乡很穷,家家的炊烟都可以透露过墙缝缝,乡亲们也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养条肥猪为过年”的日子,很少有像样的门,但不管是什么门,几乎日夜是敞开着的。一方村庄,二三百户人家,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走时顺手掩门,或是任其敞开,浑然不计谁家的母鸡在自家窝里下了蛋,哪家的小猪崽进门吃了食。要是举家出门走亲戚,在门上搭个门鼻,插根棍子,跟邻里说一起就可放心而去。谁家来了客人,又恰逢主人不在家,左邻右舍会纷纷邀至其家,盛情款待,比对待自己的亲朋还热情。谁家有个大小事,四近乡亲会尽心尽力帮衬,毫无怨言。若村里来了可疑的人物,那乡亲们的目光会使他如芒刺在背,不敢有丝毫超轨。家乡敞开的门冲淡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提炼出最浓最纯的乡情。
发生在小时候的一件事一直很清晰的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那是三叔做生产队会计那阵,由于穷,只能将每年的队里的工分账、分红账、收支单等捆放在一个破麻袋里,然后堆放在家中的阁楼上。有一次,三叔才放了半年的账被老鼠咬成一堆纸渣。这要当可是全队老少爷们命根根啊,怎么办?情急之下,三叔请全队人一一回忆,重新记账,然后一统计,居然不差分文。那时,真是山有多高,泉水就有多清,人心就有多纯。谁家丢了东西,无论多少,首先是怀疑是自己的记忆,是不是放在哪儿想不起来了,绝不会怀疑邻居,这种真诚,这种信任,是经历了世世代代的培育才有的。
路不恰遗、夜不闭户是家乡淳朴乡风的真实写照。
自从通了电与公路进村后,金银花香弥漫着整个村庄,家乡富了,村前院后左邻右舍接二连三的竖起了漂亮宽敞的红砖楼,添了新家具,电视机、摩托车等,门也自然换成了各种材质的,但唯一不变的还是向远远近近的人敞开着。我时常在想,城里人是不是也该学学他们眼里的乡巴佬。走出家门,走出楼道,互相接触,多了解,你会发现,互相关心凝聚成的“心门”,一定会比任何高档的防盗门都要好得多。(聂庆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