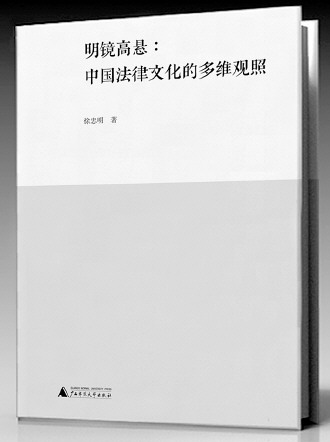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
|
具体而言,中国法律史研究,并不只是史料之搜集、耙梳、辨析与编排,而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更上层楼,对中国法律史作出更具理论意义的分析和解释。通过新问题、新方法与新理论的切实运用,推动新史料的不断开掘,提升新史料的意义解释,并在三者之间形成有效的循环互动,冀以改变目前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格局
□徐忠明
据我观察,或许不够全面,当下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可谓非常活跃;刊布的学术论著之数量,也非常可观。然而,倘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观察,似乎又有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一是史料范围好像越来越宽,种类似乎越来越多,却越来越局限于司法档案与契约文书,对其他常见史料,反而视而不见,或者视为无关轻重;二是研究主题偏重于司法实践和各种微观制度,诸如明清时期司法官员究竟是否“依法判决”这类问题,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老调重弹,论证方式亦皆似曾相识;三是除了少数被人誉为史料扎实、论证严谨的作品,很少能够读到在理论框架、概念工具与研究方法上具有开创性、刺激性的论著。在这种学术语境中,究竟如何操作方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确乎令人纠结不已。法律史跨学科研究取向不可避免
伴随着“数据库”时代的来临,伴随着“E考证”实践的展开,倘若仅仅达到“史料扎实”与“论证严谨”这两条标准,那么,较诸以往的研究,已经来得容易很多。是以,我深深感到,未来的中国法律史研究,除了继续保持这种优良传统与严谨学风,尚要更多关注其他一些层面:问题意识的凝练、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多样性史料相互释证的推进等等。不消说,这些工作的有效展开,对中国法律史学者提出了更高也更多的要求。具体而言,中国法律史研究,并不只是史料之搜集、耙梳、辨析与编排,而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对中国法律史作出更具理论意义的分析和解释。通过新问题、新方法与新理论的切实运用,推动新史料的不断开掘,提升新史料的意义解释,并在三者之间形成有效的循环互动,冀以改变目前中国法律史的研究格局。
例如,在分析帝制中国的契约实践时,我们不仅要解读契约文书蕴含的概念、功能和意义,而且要分析不同契约文书之措辞和“吉祥语词”所蕴含的签约双方的情感因素与文化意蕴;进而,还要考究契约实践之于社会秩序的维系与变化的实践价值,乃至民间契约与国家律令之间的制度关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还要提出能够超越英国法律史家亨利·梅因在《古代法》中概括的“从身份到契约”这一著名社会发展公式的理论命题,以期概括帝制中国的社会类型与秩序结构。根据我的初步考察,帝制中国实际上是“纵向身份与横向契约”构筑而成的复合结构;这一结构是建筑在“国家律令与社会契约”的双重规范之上的。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契约文书、契约实践与契约秩序来谈论帝制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类型与秩序特色,恐怕难以探知历史真相。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意味着史料范围和史料种类的拓展,而且意味着不同学科之分析技巧的运用。
这样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必将跨越法学和史学的固有藩篱而转向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与文化史等领域。换言之,跨学科之研究取向不可避免。我相信,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对中国法律史学者之提出新问题、挖掘新史料、尝试新理论、运用新方法,必将带来新机遇、新挑战和新期待;同时,也必将对他们提出更高的学术要求,包括进行更多的学术训练。由此勾勒和描述的中国法律史图像,也将变得更丰富、更厚实,亦更令人信服。跨学科与多样性史料的研究旨趣
以往,我给自己的学术定位,是在“边缘”思考,不凑热闹,不随同附和。而现在,虽然仍旧保持这样的学术姿态和研究兴趣,但是“边缘”的界域,已经有了不小的拓展,不再局限于“法律与文学”这一狭隘题域。当学者在梳理精英阶层的法律思想时,我所关注的是小民百姓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心态;当学者在解释明清时期司法官员究竟如何“依法判决”时,我所关注的是他们具有怎样的法律知识以及这些知识如何影响他们的司法实践;当学者在一窝蜂利用司法档案时,我却利用正史“循吏列传”这类看起来最寻常、最平凡,甚至为学者所“不屑一顾”的史料,冀以解释那些两千余年来备受帝国官方认同和赞誉的地方官员,他们的司法特点与典范意义究竟何在的课题;当学者在检讨常规司法实践时,我却研究“权宜司法”的政治意义和法律意义究竟何在的话题,或者说,我希望通过研究“例外”来深化对“常规”司法实践的理解。这里的“权宜司法”,是我正在写作的《权宜司法与政治控制:清代杖毙考论》这本小书的核心问题;当然,它也将展现相关法律问题的社会文化意义。足见,所谓“边缘”云云,不只指涉史料运用和学术姿态,而且指涉中国法律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概念工具、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它的意涵颇为丰富,研究起来亦颇不容易,却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因为这也是推进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一条可能路径。
收入本书的十篇论文,是我近来的思考和写作的积集。虽然不敢自誉有何特殊的创获或贡献,但也敝帚自珍。这是因为,本书可以代表本人的些许努力之所在。
本书所涉内容,既有概念解读的文字,也有人物考证的篇什;既有史事考证的文字,也有文化解释的篇什;既有制度梳理的文字,也有司法实践的篇什;既有律条和档案的分析,也有诗歌和小说的研究,甚至还有器物和图像的解读。如此等等,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跨学科与多样性史料的研究旨趣。高悬的明镜与观照姿态
写到这里,尚有必要做点“破题”工作。书稿之所以取名《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首先是因为里面收有一篇相关论文,其次是因为它能够涵盖本书的旨趣。这里所谓“多维”,系指本书涉及的史料、问题、方法与理论,比较驳杂,符合“多维”的外在标准。希望通过“多维”来观察中国法律的历史真相与若干特色。具体而言,是透过文字表达来解释思想观念,透过律例制度来理解社会秩序,透过实践行动来把握行为策略,透过人物塑造来理解文化意义,透过器物和图像来揭示文化特色,如此等等,不烦细述。要而言之,存留至今的各种史料,既是古人观察社会与实践、描述现象与事实、表达思想与情感的痕迹,也是我们透过史料丛林考察当时的社会现象,理解古人所思所想的凭据。凡此,均离不了历史学家“透视”史料的敏锐目光。
然则“观照”又有何意?在《说文解字》中,许慎释“观”作“谛视也”。在《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对“观”作了进一步解释:“榖梁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凡以我谛视物,曰观;使人得以谛视我,亦曰观。”在《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一书中,英国学者柯律格说:古典中国的“观”,具有审视或仔细检视的意思,这是《说文解字》已有的解释。在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下,“观”又获得了“内观”这一省思冥想的意义。对“观”的特点,柯律格接着说:不仅“观”的主体具有固定的视点,目光特别有穿透力,能够看到更多或更深的东西;而且“观”还意味着一种颇有人文化的考察事物的方式,从而与农民、妇女、稚童的“看”有着社会文化上的差异。足见,“观”的意蕴颇为丰富。许慎释“照”作“明也”。倘若我们将两者结合,那么“观照”即一种具有深度的观察事物的方式,不但具有察照事物的意味,而且还有反观自我的意思。就此而言,它与“明镜高悬”也有意义上的关联。这样一来,正标题与副标题就获得了相互解释的意义。
进一步说,法官与历史学家都需要有一面“高悬的明镜”,亦都需要采取一种“观照”的研究姿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揭破案件真相与历史真相。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实际上,法官与历史学家的工作性质具有天然的相同之处。所有这些,便是本书命名的全部理由。一言蔽之,本书之命名,象征着帝制中国司法官员以“明镜高悬”或“观照”来揭破案件真相,与现代历史学家以“明镜高悬”或“观照”来透视历史真相的双重意义。
表面看来,我像狐狸,一会儿研究这个话题,一会儿涉足那片领域;但实质上,我觉得自己更像刺猬,近十余年,一直埋首在明清时期法律文化这片不大的园地里默默耕耘,尝试用各种史料以研究各种话题。只不过,伴随着史料运用的渐次丰富多样,编织出来的这块明清时期法律文化的地毯,也变得日趋宽阔,色彩更加斑斓;与此同时,这块地毯也变得更加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