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司法思想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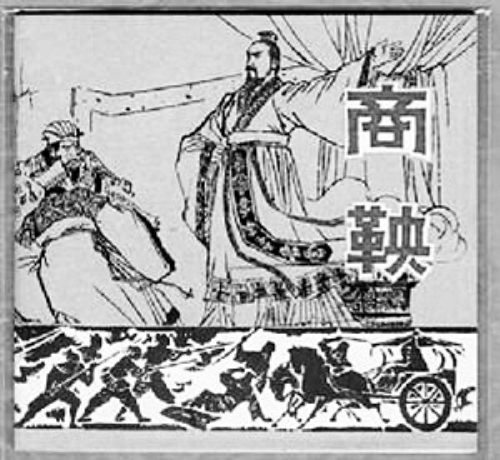
作为先秦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商鞅的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后世均影响甚巨。他携《法经》入秦,佐秦孝公进行变法,并主持制定《秦律》,为秦一统天下打下了基础。迄今为止,学界探讨商鞅法律思想的文章可谓不少,但罕有专研其司法思想者。本文略作尝试,专从司法思想的角度对《商君书》加以考察。
重罪重罚
商鞅司法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重刑”,重刑的实质在于轻罪重罚,利用刑罚的暴力性和威慑性来树立司法的权威,以巩固政权、稳定社会。因此可以说,重刑主义指向的是一种司法严酷主义。
商鞅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此所谓“重刑”是指轻罪重罚,“连其罪”是指连坐,即株连无辜。商鞅又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这里的“重罚”也是指轻罪重罚,统治者轻罪重罚,老百姓就会为其卖命。
根据商鞅的政治逻辑,统治者只有信奉重刑主义,坚持轻罪重罚,天下自可大治。轻罪重罚,百姓就不敢犯轻罪,既然不敢犯轻罪,重罪就更不敢犯了。最终,刑罚就可措置不用。如其所说:“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从刑事司法的角度看,上述言论最为精确地概括了商鞅的刑事政策和司法理念,根据这一司法理念,严酷的司法对于治理好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轻缓的司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导致“事生”与“国削”的下场。所谓“重重而轻轻”是重其当重,轻其当轻,即对重罪施以重刑,对轻罪施以轻刑,商鞅认为这种做法过于软弱,不利于树立司法的威严,而只有严酷的司法才会带来“刑去事成”的良好效果。
下面一段话还是讨论重刑问题,并将重刑与连坐加以关联:“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在这里,株连无辜的“连坐”也成了重刑的必要条件之一,这种类似于对不作为犯罪的惩治导致许多无辜者陷于暴虐的司法之网中,受到刑罚的摧残。而秦代的司法实践并未证明商鞅上述理论的合理性,严酷的重刑和连坐实际上并未使犯罪率降低,刑罚的变本加厉似乎也进一步刺激了犯罪的恶性升级——后来的秦帝国也是在“群体性犯罪”(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了。
商鞅进一步阐释其司法严酷主义(“严刑”说):“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故王者以赏禁,以刑劝;求过不求善,籍刑以去刑。”所谓“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是说清除犯罪没有比严厉的刑罚更彻底的了;所谓“以刑劝”是指“惩于彼而劝于此”,即通过严厉的刑罚使人们受到劝诫,不敢以身试法;所谓“求过不求善”,是指统治者只关注人们的罪过而不必关注人的善行,可以理解为只罚不赏;所谓“籍刑以去刑”是指凭借严厉的刑罚来达到去除刑罚的目的。这反映了商鞅对司法暴力的一种迷信。
商鞅又说:“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这与上文所言“求过不求善”的理论是一致的,不用重刑而民众能趋于善道,那是因为刑罚重的缘故。刑罚重,则民众不敢犯法,因此而致“无刑”。在商鞅看来,“刑不善而不赏善”才是一种“善治”。这样,商鞅迷失于司法恐怖主义的泥潭中,幻想通过高压与严酷的司法措施而达到“善治”,无异于南辕北辙。
必须严格依法裁判
商鞅司法思想的另一特点是“任法”,即要求法官必须严格依法裁判,既不能搞自由裁量,也不能适用其他社会规则。所谓“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即指此言。他又说:“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此处“胜法”即任法之意。商鞅尤其反对儒家那种善用道德原则指导司法审判的做法,认为儒家的礼乐、诗书、孝悌、诚信、贞廉、仁义等是“六虱”,政治活动与司法活动不可受此类东西的影响。他强调:“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这就是说重刑使司法严明,司法不严明就是因为六虱作祟,信奉六虱的法官多了,民众就很难治理了。
商鞅还指出:“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私议”指社会舆论。“释法而任私议”指统治者(包括执掌司法权力者)受社会舆论影响而放弃依法裁判,商鞅认为这会使国家陷于混乱的风险之中。
照商鞅的说法:“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刑治”是严格依据刑法治理民众,“义教”指道德教化。在治国方略上,商鞅推崇“刑治”模式,反对道德教化;在司法实践上,他反对司法官员的司法审判援用道德观念,提倡严格依法裁判。
刑罚适用要平等
商鞅司法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壹刑”,即刑罚适用上要平等。“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可见,“壹刑”就是“刑无等级”,就是要在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不管犯法者身份地位如何。上述话语透露的另外信息是:“不从王令”、“不行王法”这样的犯罪将面临“罪死不赦”的处罚,足见刑罚的苛重,反映了“壹刑”的前提是重刑。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重刑主义是商鞅司法思想中最深层的司法价值观。
商鞅司法思想反对“赦宥”。基于“刑重而必得”的立场,商鞅不但强调重刑,还强调“必得”即犯罪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商鞅明确反对赦宥,认为赦宥会破坏法制。他说:“圣人不宥过,不赦刑,故奸无起。”不搞赦宥,则犯罪者不会滋生侥幸心理,因而也就不敢以身试法。
商鞅司法思想提倡“审慎”司法。他明确提出“明主慎法制”的主张,要求君主在从事司法活动时必须审慎地依法裁判。又称“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也是要求在定罪量刑时必须高度谨慎认真,因其事关当事人的身家性命。还说:“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对法律的慎重当然也包括对司法的慎重,慎重立法与慎重司法、执法应当是君主的基本素质和心理品质。《商君书》中还有一篇《慎法》,论述了谨慎司法的重要性。
法官要通晓法律,不以私害法
商鞅司法思想又一个特点是“明法”,即要求司法官员自己不但通晓法律,还要向当事人释明法律。他说:“法治不明者,君长乱也。”意思是说糊涂的君主才不能通晓法律,当然更不能向臣民释明法律,如此也就很难实行法治。正如其另外所言“法必明,令必行”,明法是“令行”即法治得以实施的前提。又说:“夫错法而民无邪者,法明而民利之也。”“错法”即实行法治,而实行法治的关键是官员应当精通法律并向民众释明法律,这样才能有利于民众依法行事。
为了释明法律,商鞅还主张设置专门负责解释法律的官员——“主法令之吏”。他说:“各主法令之民,敢妄行主法令之所谓之名,各以其所忘之法令名罪之。……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谓也,皆以吏民之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可见,对主管法令的官吏来说,他们必须精通法律,并且严格执法,如果忘记执行其主管的法令条文,则会按其忘记的法令条文来进行处罚。主管法令官员的另一职责是向其他官员和民众释明法令,如果主管法令的官员对吏民拒不履行职责,不回答吏民对相关法令的咨询,那么吏民一旦犯法,就按吏民询问的法令条文所规定的罪名来处罚主管法令的官员。照商鞅的说法,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在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商鞅还指出:“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置法官,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故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置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这里所言“法官”应该也是主管法令的官员,此类官员既要精通法律,又有执法权(包括司法权),并且享有向吏民释明法律的权力和职责,使吏民知法守法。“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应该说,设计此种制度也有让民众通晓法律来监督官员司法活动的初衷。
商鞅司法思想强调“不以私害法”,即司法官员必须秉公执法,勿为私情私利所左右。他说:“故明主爱权重信,而不以私害法。”不以私害法才能树立司法的威信,才能推行法治。
商鞅司法思想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的。他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在商鞅看来,自利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放纵自利性,就会败坏礼法。他又说:“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照商鞅的说法,实施法治的两个抓手是赏与罚,而赏罚乃是顺应了人的好利恶害之性。刑罚作为一种重要的司法手段,乃基于人性中厌恶和躲避祸害的本能而设,而赏赐实际上也是对刑罚的一种辅助,因其可引导人们干正当的事情而不去干邪恶的事情。如其所言:“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故其国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此亡国之兆也。”这是说,刑罚用来禁止邪恶,防止人们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利益;赏赐是用来辅助禁邪的手段,它将人们的求利行为导向了合法的轨道。
归纳起来,商鞅的司法思想就是要求利用刑罚的暴力与威慑力来树立司法的权威。我们今天学习商鞅的司法思想,除了要摒弃他的以高压与残暴的司法政策糟粕外,应借鉴他提出的司法平等、不以私害法等积极的主张,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崔永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