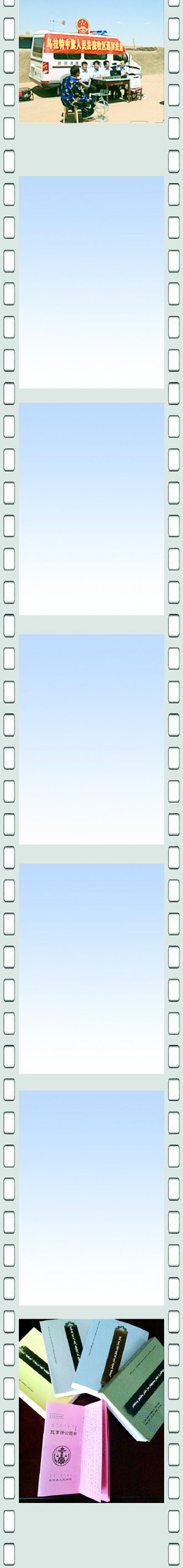双语法官巧用语言化解牧区矛盾纠纷
主题描述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越来越重视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法院审理少数民族群众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但是,能够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诉讼的双语法官短缺、整体素质也不高,制约了少数民族地区司法审判工作的开展。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加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官的培训力度,加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法院的人才扶持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双语诉讼案件原告 双语法官把我们的意思完整地翻译给对方,而且把我激烈的语气柔化了,真的很难得
双语诉讼案件被告 这场官司让我从不懂法到认识了法律,感谢双语法官
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 草原上的牧民最开始很排斥法官,我们需要的就是放低姿态,和牧民拉近距离,让百姓信任你,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明白法律的神圣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 在今后,法务翻译在双语诉讼中一定要得到重视,要作为一个机制建立完善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双语诉讼面临的法律窘境
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也都规定了这项原则的具体内容。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越来越重视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法院审理少数民族群众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法院系统缺乏既精通法律又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法官的严峻形势,又给审理此类案件带来了困扰。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加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官的培训力度,加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法院的人才扶持力度,取得显著成效。《法制日报》记者近日深入内蒙古基层法院,对双语诉讼的现状进行了探访。
阿巴嘎旗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牲畜承包合同纠纷原告陈利荣:
“双语法官怎么翻译都是个难事儿”
陈利荣,72岁,汉族,不会说蒙语,是一起牲畜承包合同纠纷的原告。经历了一场双语诉讼后,他深感双语法官的不易和难得。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怕钱要不回来,我有些激动,甚至说了一些过激的话,幸亏当时法官没有全部翻译成蒙文给原告听。”
回忆起开庭时的情景,72岁的陈利荣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和被告达木丁本来就认识,基于朋友关系,我将名下的几十头羊承包给了有草场的他,但两三年下来,不但承包费没有给我,草场维修等费用还需要我借给他。这样几年下来,他已经欠了我8万多块钱。”陈利荣说,自己只是一个工薪阶层,“这些钱如果打水漂了,对我的家庭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陈利荣回忆说,后来听说达木丁因为草场被国家铁路占用一部分,得到30余万元的补偿款,“因为他不只欠了我们一家的外债,为了防止拿不到钱,在做了相关咨询后,我起诉到了法院”。
就这样,一场蒙语汉语交替的庭审开始了。
“我在这边激动地说了一大通,由于达木丁只能听明白简单的汉语,所以基本上就是‘只闻其声不明其意’吧。”陈利荣说,当时由于情绪激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有多过分,“只是看到阿巴嘎旗的双语法官在把我的意思翻译给达木丁的时候,一片和风细雨,达木丁在那边还接连点着头。由于我听不懂蒙文,也是一头雾水”。
“后来我意识到,肯定是双语法官在翻译我的话的时候,把我的语气和措辞都柔化了,这样才能让双方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谈如何还钱。”陈利荣说,“如果双语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中,没能把我们的意思完整地翻译给对方,那么可能会导致案子审理出现偏颇,我们当事人不满意;但是如果一字不拉地都翻译给对方,由于方言或者其他因素,有可能导致本来就语言不同的双方根本坐不下来审案子。所以他们真的是挺难得。”
阿巴嘎旗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牲畜承包合同纠纷被告达木丁:
“双语法官的调解给我带来了希望”
达木丁,蒙古族,只会说蒙语。由于受灾以及经营不善,欠下外债,被其中一名债主告上法庭。最开始,得知自己成了被告,达木丁特别担心害怕。但到了法院,他的心就慢慢放下了。而双语法官最后的调解结果,可谓是给了达木丁意外的惊喜。
“当对方用你听不懂的汉语和法官陈述时,你是什么样的心情?”记者问道。
面对记者的提问,达木丁默默地看着记者,一脸迷茫。坐在一旁的双语法官苏布达赶紧用蒙文给达木丁翻译。
“觉得自己跟傻子似的(注:以下达木丁所说均为双语法官的翻译)。”达木丁憨憨地说,“甚至最开始担心法官会说假话。”
不过,达木丁的这种担心,在双语法官谨慎处理他与陈利荣之间的合同纠纷后,就烟消云散了。
据达木丁告诉记者,由于受灾以及经营不善,草场的牲畜都被自己“养没了”,政府占用草场补贴的30多万元根本补不完自己的外债窟窿,“这些外债中,只有陈利荣是诉诸法律的,也只有这笔外债是解决得最好的”。
“最开始,得知自己成了被告,我特别担心害怕。但到了法院,我的这颗心就慢慢放下了。”达木丁说,“我也听不懂,就是看陈利荣在对面很大声地说了一大通,情绪好像比较激动,但双语法官却比较缓和地告诉我他希望我能尽早还钱。我就向双语法官陈述了我的难处,提出希望分期偿还陈利荣的债务。双语法官主动承担起了在我们中间进行债务调解的工作。”
最后的结果,可谓是给了达木丁意外的惊喜。不仅将8万余元的债务分成三期进行偿还,并经商议免去了原本协议中的违约金,“协议中原本定了若不到期还钱要有本金5%的违约金,我拖了18个月没还钱,这也是好几万元呢”。
“刚一进法庭的时候,我害怕紧张,更多地是来自于对双语审理的担心。但到后来,双语法官用汉语和陈利荣进行对话的时候,我就感觉很轻松了,因为我知道法官是在尽力帮我们把问题解决到最好。”达木丁说,债务分期后,他用余下的4万多块钱又买了些羊,“这样我就可以再慢慢地把我的草场经营起来,这个希望是双语法官给我的”。
就在记者表示采访结束时候,达木丁突然走到记者面前,用蒙语说了一长串的话,随后一脸感激地望向坐在一旁的阿巴嘎旗的双语法官们。
“他说,这场官司让他从不懂法到认识了法律,感谢双语法官。前两天,有个债主到他家去拿钱,不仅提走了全部债务还有利息,还在走的时候骂了他一通,法院审理的这起债务是所有债务中处理得最好的。”苏布达向记者翻译说。
内蒙古阿巴嘎旗人民法院民事庭庭长苏布达:
“调解为上”的牧区双语巡回法庭
苏布达,1983年参加工作,1987年年底来到内蒙古阿巴嘎旗法院,开始下乡办案。1990年成为助理审判员,开始双语诉讼的审判工作,在草原巡回法庭工作了25年。25年的审判经历让她深刻体会到,在语言因素之外,“信任”是巡回法庭双语诉讼必备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风很大,冬天草原上的风都卷着沙砾,吹到脸上生疼生疼的。我年轻的时候更瘦,分羊的时候只能使劲拽住羊圈的门栅栏,要不然我真能被风吹走。分完羊,晚上9点多了也没饭吃,我们就讨了面条,下了吃了”——这是调解离婚之后,在帮助牧区百姓进行财产分割;
“四五平方米的蒙古包里,虽然是女同志,但借宿的时候也只能和当地牧民混居在一起。以前草原上的蒙古包只是在地上铺层毡子,湿、硬,再混合着汗味,我就找个角落蜷缩一晚上。草原上有狗,夜里我也不敢去方便,只能少喝水,忍着”——这是在草原巡回办案的过程中,夜宿牧民家的情形;
“个别当事人对法院工作不了解,尤其是离婚案件、涉及家庭财产纠纷的,一看法院的人来了,看都不看你一眼,甚至还有掉头就走的。有个离婚官司的男方,看到我们来了,带着孩子骑上摩托车就走了。草原上我们上哪找去啊,只能托当地有威望的人找回来,一等就是一天”——这是在草原巡回法庭办案经常碰到的“特殊”情况。
“双语诉讼一般都涉及到牧民当事人,而牧民大都分散居住在千里草原,有时想找当事人、证人或送达法律文书等都非常困难。上诉人在中院上诉立案后就没了踪影的情况也是经常遇到,所以涉及到双语诉讼的案件,有时很难按照审限结案”——这是巡回法庭的法官们无可奈何的“不依法”;
……
在草原巡回法庭工作了25年的苏布达,向记者描述上述情景时,甚是轻描淡写。对于她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地平常,甚至是理所当然。
“1983年参加工作,1987年年底来到阿巴嘎旗法院,开始下乡办案。1990年成为助理审判员,开始双语诉讼的审判工作,一直到今年才调到了民庭,就是年纪大了,实在干不动了。”记者眼前的苏布达虽然已年过半百,但语速依然很快,声音时不时激昂起来,与其不足155厘米的瘦削身材似乎有些“冲突”。不过声调再起伏,苏布达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给人以亲切之感,“这可能和我在草原上办案有关系”。
对于这其中的关系,苏布达解释说,草原上的牧民最开始很排斥法官的,“觉得有案子就是没好事,我们需要的就是放低姿态,和牧民拉近距离,让百姓信任你,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明白法律的神圣”。
说到信任,苏布达告诉记者,“信任”是巡回法庭双语诉讼必备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由于人员缺乏,在庭审当中,一般就是讲汉语的一方当事人陈述完后,法官要把他的话翻译给讲蒙语的一方当事人,而讲蒙语的一方当事人的陈述,法官又得把它翻译给讲汉语的一方当事人,同样的话等于说了两遍,开庭的时间自然延长一倍不说。这期间,法官更多时间是在充当翻译角色,有时还得翻译文字。”苏布达告诉记者,如果当事人不信任你,那么就有可能对于你翻译的话提出意见,“而且,由于蒙语和汉语在语言上的极大区别。有时候汉语一句话,需要蒙语十句甚至是二十句进行翻译。反之也是一样。需要翻译的一方可能就会想,我说了那么少或者说了一大通,你法官怎么和对方说了那么多或者才说了这么一句。原被告有一方对庭审表述有意见,这个庭就开不下去了”。
而另外一点很重要的是,苏布达告诉记者,在草原双语诉讼的巡回法庭办案是以“调解为上”,“2012年至今,阿巴嘎旗法院审理的120起案件中,有119起是调解结案的”。
“说起调解结案,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除了案情需要外,也是因为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制约的。”苏布达坦率地说,“相对来说,牧区牧民的法律素养有待提高,再加上幅员辽阔,有时候当事人起诉之后就半年找不到人了,而调解结案可以省去诉讼中的诸如质证等很多环节,也可以‘规避’诉讼时效的一些法律问题”。
“我们这也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吧。”苏布达笑言。
虽然现在已不在草原上开庭,但仍在继续着双语诉讼工作的苏布达,对于双语诉讼特别基层法院的工作前景也有着自己的担忧:“因为双方当事人语言的不同,所以提供的证据材料也常常是两种文字、法庭当庭举证质证,就得把这些证据全部翻译成双方当事人能看得懂的东西。两种语言带来的问题很麻烦,有时候用同一种语言文字的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清楚的东西,在翻译时却很难准确的翻译出原来的意思,很容易走样,尤其是在涉及到法律专业用语的时候,不具备法律职业背景的翻译常常译得风马牛不相及。”
“干双语法官,累是累,但办完案心里踏实。我们都会继续努力的。”对于自己过去的25年,苏布达这样说。
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宝宪:
力促双语人才不断层不断档不断岗
身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黄宝宪,一说到双语诉讼人才短缺的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他说,因为双语法官短缺,不能组成合议庭,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基层法院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前年院里聘了三个书记员,还选聘了两个应届大学生,希望以此来填补双语诉讼中的人员缺口。现在呢,人一个不剩全走了。现在院里只有一个懂蒙文的书记员,哎!”
一声长叹,端起水杯,仿佛时间静止,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宝宪盯着自己的水杯不再说话。
几分钟的时间,很短,但在这样的气氛下,却很难熬。
“记者采访,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了,但说到双语诉讼人才短缺的问题,我这情绪还是时不时会激动起来。”情绪平复下来的黄宝宪,向记者微微一笑。
近些年,锡林郭勒盟经济发展迅速,汉语越来越普及,很多蒙古族群众汉语水平提高较快,蒙语相对生疏;而蒙汉群众交往增多,草场租赁、牲畜承包、民间借贷等经济往来增加,引发的诉讼也增多,诉讼双方使用双语诉讼已成为普遍现象。
“近三年全盟双语案件数量为3497件,其中锡盟中院568件。尤其是民事案件可以说数量是翻着番地增长,但人员数量却是‘纹丝不动’。”黄宝宪向记者透露说,辖区内有的检察院曾经想在全区范围内招考几名双语专业人才,结果因为没有人报名而流产,“基层法院检察院条件落后,缺乏与大城市、发达地区的竞争力,也是基层人才困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了解,因为双语法官短缺,不能组成合议庭,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基层法院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为了保证案件的依法审理,各院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如从别的庭临时借调法官,把不懂双语的法官拉入合议庭充数。有的法院为了缓解双语法官不足问题,就专门配备了一名翻译,作为‘自由人’,哪里需要派到哪里。”黄宝宪说,有时,锡盟基层法院还在每个苏木(蒙语中指“乡”)聘请一名人民陪审员,“近年来基层法院招考公务员,要的全部都是能够使用双语的人才,但能招进来的很少,现在连许多蒙古族的孩子也已经不会讲蒙语。基层法院里精通双语的法官常常留不住,不是被政府部门提拔使用,就是流动到了上级法院工作,这也使双语法官本来就短缺的基层法院更加雪上加霜”。
“在锡林郭勒盟地区,法院一般没有专门的翻译。若法院聘请双语翻译,就会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所以,双语诉讼大都成了懂双语的法官一边翻译一边审理。”对于这样的又当翻译员又当审判员的“不合理”状况,黄宝宪显得很无奈,“根据法律规定,翻译人员要有相应的资质,但多年来,从事双语诉讼的法官忙于诉讼业务,职级走的又是法官序列,很少有人去参加翻译资格的考试。而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有人开始质疑法官的翻译资质,这也可能成为一段时间困扰双语诉讼的一个重要问题。”
黄宝宪坦言,全盟双语法官近些年参加的双语培训很少,几乎为零。
此外,即使能够熟练地使用双语开展诉讼活动,但制作双语法律文书又成为了目前诉讼中存在的一大瓶颈。
“双语法官助理不能独立办案,不能参加合议庭,没有表决权。院里的其他法官要么是能说不能写,要么是精通蒙语而汉语又不太好。”黄宝宪说,双语诉讼法官的翻译“职责”也对双语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现状是有关蒙语的法律培训资料基本没有,一些蒙语的法律培训班授课老师也往往是用汉语进行讲授。而目前在内蒙古的大学法律教育中,也只有很少的学校的法律专业使用蒙语授课。这就造成双语审判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局面,“如阿巴嘎旗,本科全日制学历不到10%。锡林郭勒盟是自治区使用双语诉讼最普遍的地区,除了东南部的多伦县主要使用汉语开展诉讼活动外,其余的11个旗县市都涉及到双语诉讼。现在全盟共有法官377名,其中汉语法官109名,占法官总数的28.9%,是全区平均数的四倍。锡林郭勒盟也是自治区开展双语诉讼最好的地区之一”。
经过长期的调研,黄宝宪向记者表示,从锡盟两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情况看,既懂语言、又通文字的蒙汉双语法律人才已不能满足实际工作需要,不能满足群众的诉讼需求,不能充分保证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落实,并直接影响到审判工作。
“现在继续建立双语人才培养工作机制,力促双语人才队伍不断层、不断档、不断岗,确保双语人才队伍更加合理、结构更加优化。在培训方式、培训制度上,也要进一步研究,长短结合既抓短平快,又要抓长期性、基础性、连续性的培训工作。”黄宝宪建议说,还应推进政法院校招录体制改革工作,扩大少数民族地区法院“双语生”的招生规模,重点解决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法院双语法官短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继续推动人员招录办法改革和司法考试改革,拓宽双语法官来源和渠道,完成法官员额编制标准和法官职务序列改革。逐步建立并完善双语法官择优遴选制度和有利于基层干警成长的选拔机制,进一步解决一些基层法院案多人少、双语法官断层、人才流失等问题,落实法院经费分配保障办法”。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萨仁:
双语诉讼中的翻译困惑亟待破解
为了尽量弥补双语人才的不足,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相关人才编订了自治区第一本《汉蒙法律名词术语辞典》,并完成了四部总和超过80万字的蒙语法律材料。萨仁向记者介绍时如数家珍。不过,身为内蒙古高院审委会专职委员的他,对完善双语诉讼,有着更高的期待。
在内蒙古,一些蒙古族居民不大会说汉语,而汉族居民又不会说蒙语。每当他们到法院打官司,法官就同时用两种语言为他们进行诉讼,这就是双语诉讼。运用双语进行诉讼活动,在我国西部的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较为普遍,不仅方便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当事人,还有效维护了其合法权益。
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 “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还有我们自治区出台的蒙古语言文字的一个条例,这些都是法院等司法部门开展双语诉讼的一个立法保障。”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萨仁向记者介绍说,“在双语的使用上,法院等司法机关在各行业各领域都是领先的。”
“现在就出现过蒙古族的群众到银行办业务,签的是蒙古语,银行不认导致无法办业务,从而产生纠纷闹到法院。而这种情况在法院系统是不会发生的。”说到这里,萨仁语气肯定地表示,“从我1985年工作至今,我们没有一起案子是没有给有需要的当事人提供语言方面的诉讼保障的。”
萨仁向记者介绍说,内蒙古高院现在正逐步在案件的各个环节完善双语诉讼,“比如说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立案大厅建设完善专门的双语诉讼窗口,在其他地方选择性地直接配备双语立案法官,以此在案件的最初环节向当事人提供相关的诉讼风险提示、诉讼指南,使之明了自己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等等”。
采访中,萨仁向记者坦言,在基层法院,由于各种原因,双语法官人才十分缺乏。“近年来,通过对双语法官的培养和培训,一批这方面的青年人才进入高院,为双语诉讼的推进起到了极大地积极作用”。
“但是,我们又有新的困惑,就是法律文书法律材料的翻译工作。”萨仁举例说,“高院有需要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案件,当涉及双语诉讼的案件,有可能从一审到二审都是蒙语文书,高院业务科和翻译科的工作人员就需要将审理过程中包括预审材料、公诉材料、承办人的承办报告、合议庭记录等需要上报的材料全部翻译成汉语,往往就是十几本卷宗,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可想而知,加班加点也就成为了‘理所当然’”。
萨仁说,更为需要注意的情况是,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权威性的蒙文法律资料,所以在双语翻译的过程中极为艰难,“两种语言带来的问题很麻烦,有时候用同一种语言文字的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清楚的东西,在翻译时却很难准确翻译出原来的意思,很容易走样,尤其是涉及到法律专业用语的时候,不具备法律职业背景的翻译常常译得风马牛不相及”。
“比如说,曾经在一起案件中,一份蒙文证据,懂蒙文的一看就是一份遗嘱,是关于遗产的处置问题,可这份证据经过有关部门翻译成汉语后,却变成了委托代管,遗产处分关系经过这么一翻译变成了委托代管关系。”萨仁说,甚至一些有法律背景的翻译人员,因为对案情不全面掌握或翻译者缺乏审判实践经验,在案卷、证据的翻译过程中同样容易出现问题,“而蒙文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资料的缺乏也造成了翻译人员甚至法官在翻译实践中缺乏依据。如‘担保、质押、扣押’,即使是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把它们翻译成蒙语也只能是个大概意思,很难把它们之间的区别明确界定。所以,就出现了不同法院或不同法官翻译出的法律版本千差万别”。
萨仁向记者介绍说,为了尽量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内蒙古高院组织双语诉讼的相关人才编订了自治区第一本《汉蒙法律名词术语辞典》,并完成了四部总和超过80万字的蒙语法律材料,“但即使如此,在现如今司法解释层出的情况下,双语法官能够学习的资料数量太少,更新得太慢”。“我认为,在今后,法务翻译在双语诉讼中一定要得到重视,要作为一个机制建立完善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双语诉讼面临的法律窘境”。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现在翻译人员不够的情况下,法官‘翻译’的局面还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萨仁说,双语诉讼法官的翻译“职责”也对双语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现状是有关蒙语的法律培训资料基本没有,一些蒙语的法律培训班授课老师也往往是用汉语进行讲授。而目前在内蒙古的大学法律教育中,也只有很少的学校的法律专业使用蒙语授课。这就造成双语审判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的局面,“我认为可以与大学合作进行双语诉讼人才的定向培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精通蒙语、汉语,同时具备全面法律知识的双语诉讼人才”。
最高法院推进双语法官培训
遴选法官巡回授课
2006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从本院审判部门和部分高院,遴选法学基础深厚、审判经验丰富、工作实绩和授课水平都比较突出的优秀法官,组成最高人民法院讲师团,赴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法院开展巡回授课活动
办双语法官培训班
从2008年开始,国家法官学院每年举办一期少数民族中青年法官培训班,至2010年共培训少数民族法官350余人。在政策上和经费上,最高人民法院对少数民族法官培训给予支持
着手编写培训教材
2009年,青海、内蒙古、新疆等我国部分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法院已经着手双语法官培训教材的编写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统筹协调并投入资金,促进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区双语法官培训教材的编写
研究建立培训基地
2011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养力度,积极研究建立双语法官培训基地
继续加大扶持力度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法官”培养力度,积极研究建立“双语法官”培训基地,通过深化东西部法院横向交流,举办培训班,加大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法院的人才扶持力度
以上材料来自相关报道
余飞整理
图①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双语”法官在办案。刘忠 张贵摄 图②为内蒙古高院组织编写的双语法官培训材料。赵丽摄
(记者 史万森 赵丽)
·湖北襄阳:让法治的阳光力促矛盾化解
·贵州对重大矛盾化解攻坚再动员
·同安法院外来员工纠纷援助中心:将矛盾化解在源头
·海南陵水社会“网格化”管理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绵竹经验:完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
·绵竹:如何把矛盾化解到群众身边
·绵竹:如何把矛盾化解到群众身边
·社会矛盾化解: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
·湖南怀化:“信访事业当家业”矛盾化解在基层